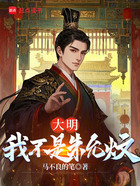
第23章 来复
“指挥使,人抓住了!”
夜深了,天穹之上悬挂一枚弦月,
薛定善突然闯入朱允炆临时办公的公房,大声喊道,
“首恶已缉拿归案,指挥使大人是否亲自审讯?”
朱允炆揉了揉自己的脑袋,在锦衣卫翻看了一下午卷宗,触目惊心,令他有些头晕:
“在哪里抓到的?”
薛定善面露喜色:“是在那逢初寺旧址之上,那和尚突然回返,被属下抓了个正着。”
“看来是我想多了。”
朱允炆当即起身,对许三嘱咐道,
“叫人把林大喊回来。”
朱允炆问道:“赃款追回了吗?”
“不曾。”
“一个和尚,几个乞丐,就能卷走一万多两白银,虽然大部分是宝钞,折损下来,也有九千多两。”朱允炆叹了口气,“没关进诏狱吧?”
“没有,正在监房之中,等待指挥使大人提审。”
薛定善低着头,目光闪烁不定,
“属下知道太孙不习惯诏狱之中的味道。”
薛定善的态度来了个急转弯,朱允炆还有些不习惯:“我还是比较喜欢你之前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
薛定善只是摸了摸脑袋,没再言语。
百户开路,进监房时,来复盘腿坐在地上,双眼紧闭,
他身上衣服整洁,似乎没有任何进行过激烈且行之有效的反抗,
薛定善冲过去,一脚将他踢翻在地:“指挥使大人来提审你了,还不醒。”
来复睁开眼,掸了掸身上的灰尘,道一声“阿弥陀佛”,随后才看到朱允炆的脸庞,面露异色:“是你?”
朱允炆坐在许三搬过来的椅子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来复:“如果我是你,我绝对不会回来。”
来复笑了笑:“我不是乱党,回来是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所以......在那天之前,你们就盯上我了?”
他环视一周,没找到那个面容枯槁,身材枯瘦的中年男人:“那个人,他不在。”
“他不是锦衣卫的人。”
朱允炆说道,
“钱哪里去了?”
“哦......”来复笑了笑,“自然是拿来修缮寺庙了。”
薛定善怒道:“屁话,你根本没去买砖!也没请力工。”
他查的清清楚楚,
虽然锦衣卫有皇权特许,先斩后奏之权,但一应证据,流程都有档案封存,经得起皇上和指挥使查看,
除非特别紧急的大案......
这种小案子,没有人不会留存证据。
来复认真地说道:“是的,我没在金陵城中请工匠。我请了杭州的瓦匠,苏州的木匠,北平的花师和山东的泥匠,他们不日将会来到金陵城中,前来修缮寺庙。”
“你废话!一个月前你来到金陵城.......”
“你闭嘴!”
朱允炆斜睨着薛定善,
“许三,我说话的时候他再插嘴,就替我掌他的嘴!”
“是。”
许三恭敬领命,瞪着眼睛看薛定善,
这位向来以暴躁著称的百户缩了缩脑袋,紧紧闭上了自己的嘴巴。
“来复,你既然薄有诗名,又有些佛名,金陵城中知晓你善名的商贾文士和官员都不少,你为何要行此乱党之事?”
“我不是乱党。”来复定定地看着朱允炆的眼睛,“我一心礼佛,问心无愧。”
“那你收养乞丐,是为了做什么?”
来复沉默着,没有回答:“......”
“经锦衣卫调查,你收养乞丐供他们吃饭,教他们识字,专找商贾下手,窃听他们家中私事,转头便以【高僧】之名,为他们破除心中迷障,可有此事?”
“嗯,确有此事。”来复毫无凝涩,当即承认,“阿弥陀佛,天下哪有未卜先知之人。”
朱允炆厉声道:“你搜集情报,扰乱治安,制造恐慌,以诗会之名大肆敛财,却不以修缮佛寺之用,还不是乱党?”
“我收来善款,皆用于修缮佛寺。”
“钱款流向,可有留证?”
“无有。”
朱允炆在心里叹了口气,转头看向薛定善,
“把你收集整理的官员名单拿出来,让他瞧瞧。”
薛定善当即从袖中掏出了一张折叠起来的宣纸,
上面是锦衣卫重点监视监控盯防的朝中大员和各省大臣,
朱允炆亲自接过信纸,将它递交给来复,
“来复,你是否和这些朝堂官员有私下来往。”
来复再一次仔仔细细地看了不长的名单,摇了摇头:“不曾,指挥使大人,我不曾和这里面的任何人有来往。”
“一个都没有?”
“没有。”
来复目光炯炯,他已涉事政商,但还未到能接触这些人的层次,即便想牵线搭桥也未到时候,
看着来复的眼神,朱允炆在心底叹了口气,他知道这个和尚说得是真话,
果然如他所料,来复不是乱党。
“锦衣卫将你捉来,你可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莫要信口雌黄,牵连他人!”
朱允炆眼神澄澈,
来复啊,若你不是作奸犯科,与朝中之人密谋反叛,我都可以救你......
但你若是和邪教勾结,我便没有办法救你了,
朝中这些人,可是已经在锦衣卫“挂了名”的乱党,
你可不要负隅顽抗,被屈打成招啊。
许三厉喝道:“老实交代!”
来复双手合十:“指挥使,我认罪,我以礼佛之名收敛钱财,实则另作他用。”
“做什么用?”
“赈济灾民。”
“灾民自有各地官员开仓赈济,需要你赈济灾民?”
“各地官员尸位素餐,借天灾大肆敛财,各地遭灾之后,反而比遭灾之前更加凋敝。”
“你信口雌黄!”
“是不是,指挥使一观便知。”
“锦衣卫自有定论。”朱允炆震声,“赃款流向何处?”
“已于谢记米行购买米粮,星夜发出。”
“好,薛定善,速去查!此前你在杭州府,也借善名曾大肆敛财,部分修缮寺庙,其他的流向哪里?”
“也购买了赈灾米粮,去岁山东遭灾,民不聊生!”
“去查!”
朱允炆拍案而起,
“你已购买多批大笔米粮用于赈灾,为何不与官府合作。”
“官员贪腐。”
“听到了吗?官员贪腐!”朱允炆对锦衣卫怒喝道,眼眶有些红了,“成日里在京城打转,说是监察百官,你们监察了个什么?查!山东,淮南,河南的各地主官,一个个去查!”
“指挥使大人,镇抚司内的千户都有要是在身。”
“那你们百户去查,查的好,我禀报圣皇,升你们做千户!”
薛定善面露喜色:“遵旨。”
真是敛财救灾,可他们为何要遮遮掩掩?
热血上涌,朱允炆感觉自己脑子有些不清醒了:“将他押入诏狱,莫要问刑。”
旋即他强忍着心里的恶心,转身离开。
许三紧跟在太孙身后,终于憋不住内心的疑问:“太孙,为何不继续审问了?”
“若他是乱党,他既然敢来,已经存了必死的心志,问一个必死的人,他只会告诉你他想让你知道的事情。”
“但他也想活。”
“对,他想活。”
我也想他活,这样的人不该死。
朱允炆坐在自己的临时公案之后,端起茶杯狠狠喝了几口,调匀呼吸,
他的目光越过北镇抚司衙门,越过六部衙门的高墙,看向了漆黑的天空,
元明时期,有一个教派流毒极大,屡禁不止,堪称蚀骨之蛆,
但流离失所的百姓们却又从中得到了不少心理安慰,
所以直到明朝灭亡,清廷时期,它依旧能聚集起无数百姓,形成一股强大的民间力量,流窜行动,教众无数……
直到清末,这个残存的教派这才转变成了其他形式,
但后来的义和团,太平天国甚至救国会里也有他们的影子……
这个教派叫白莲教,从元末起,它就像是一个幽魂一般,游荡在神州大地上,
朱允炆希望募款救灾只是来复个人行为,与白莲教无关,
因为如果来复真的和这个邪教有关,那么这个善良的和尚一定活不了,
来复是个好人,但他做的事,会动摇国本,
就算朱允炆不是锦衣卫的临时指挥使,也是皇帝的亲孙子,
一个人不可能既享受着皇室的特权,又能和底层人民有一样的利益诉求,
朱允炆将茶水喝光,许三便给他补上:
“太孙,你还不休息吗?”
“传我的令,将在京的所有千户百户全部召集过来,我要彻查金陵城中的和尚和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