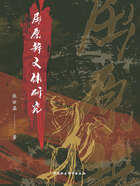
第二节 士人个体创作下的文体生成
从春秋到战国晚期,在这几百年战乱频繁的历史时期,相继涌现出了一大批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精英个体,包括卿士大夫、行人、史官、诸子、纵横策士等。他们对于宗周及各诸侯国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一方面学习和继承着统治阶层经典文化,一方面又创造、丰富着经典文化。相对于仪式活动场合中的典章文诰,他们的文辞创作较为自由,文辞之中融入了他们的个性才智与创作构思,使文辞在文本结构上、语辞形式上表现出了一些个性化的特征。
一 “喻巧而理至”:卿士大夫的谏说文
在我国古代,卿士大夫于一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向内能匡正君主,谏政议说;向外据理护国,应对诸侯,接遇宾客,因而常被视为国之栋梁,君之股肱。多数情况下,他们所依凭的正是言辞、文辞,即所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34],如楚国屈完凭言辞力却齐桓诸侯大军。这样的言辞多是卿士大夫个人才智的体现,创作的个性化特征明显,无制度规范约束,在创作动机、功能及使用场合上与仪式、礼制下的文辞创作有明显的不同。卿士大夫的这类言辞,多保存在《国语》《左传》中。
《国语》和《左传》是两部史书文献,成书时间大约在春秋末至战国初期。就这两部书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学界普遍认为是作者收集史料而进行的整编加工。如唐人刘知几在《史通·申左》中云:“《左氏》述臧哀伯谏桓纳鼎,周内史美其谠言;王子朝告于诸侯,闵马父嘉其辨说。凡如此类,其数实多。斯盖当时发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语,就加编次。亦犹近代《史记》载乐毅、李斯之文,《汉书》录晁错、贾生之笔。寻其实也,岂是子长稿削,孟坚雌黄所构者哉?”[35]刘知几指出《左传》中的一些文辞为编者采原有史料而编次,其眼光不可谓不敏锐。陈桐生通过自己对《国语》的研究,则指出:“《国语》是一部主要记载卿士大夫治国言论的原始史料汇编。”[36]我国史官制度发达,《国语》与《左传》的编纂成书,无疑得益于这些浩瀚的历史史料文献,今天我们虽然已经看不到西周春秋史官对卿士大夫、行人言辞、事迹的原始记载,但通过《国语》《左传》还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还原。诚如刘知几所说“臧哀伯谏桓纳鼎,周内史美其谠言”等乃是编者依据原有之史料而来,《左传》中确实保存了大量的卿士大夫们的言辞原文,以记言为主的《国语》,这一点更为明显。卿士大夫的这些辞令,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散文文体,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相对于西周时期仪式、制度规范下的文辞创作,卿士大夫的谏说之辞,语言简易明了,个性化特征明显,文学性色彩更为鲜明。并且为了达到谏说的目的,言辞显然经过了一定程度的构思。
根据《国语》和《左传》的记载,卿士大夫的这些言论多发生在进谏君王,或者与他人的论辩、问对中,看似具有随机性,实则不然。翻阅《国语》与《左传》,会发现,卿士大夫的每一次论说往往与一定的事件相关联,这些事件有大有小,小的具体到君王过错、违礼背俗;大的则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卿士大夫的言辞多为针对事件而发,或是谏君归正,或是聘盟问答,或是为国排忧解难。这种言辞靠的就是一己之渊博学识、独特的见解以及出众的口才,因而具有一定的个体独立性,而不再是一种集体意识的体现。如《国语》中的《邵公谏厉王弭谤》《王孙满观秦师》《蔡声子论楚才晋用》等等;又如《左传》中,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成公三年《知罃对楚王问》等等,都是如此。而且,卿士大夫的这些文辞,在讲述之前是经过了自己一番构思的,如《邵公谏厉王弭谤》篇中,厉王暴虐,且不允许国人议论指错,还命卫巫监国人。对于厉王这一荒唐举动,邵公在谏说之前必然早已知晓,而且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当厉王向他炫耀“吾能弥谤,乃不敢言”时,邵公则顺理成章地把他已思考好的说辞,陈述出来,而不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的即兴劝谏。又如《烛之武退秦师》中,烛之武见秦伯之前,对于如何言说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以劝退秦师,也必然是有构思的。因为秦晋围郑在前,郑伯听佚之狐之言,专门找到了他,且此事关乎郑国存亡,在去见秦伯之前,策划好自己的说辞,是合乎常理的。他们的这种构思虽然不是主观为文学,但与文学的构思在客观上具有相似性,而当这些言辞被卿士大夫本人或史官记录、追记下来时,就是一种文体的形成,因为有个体的构思在,所以更接近文学文体。如《邵公谏厉王弭谤》中邵公的谏辞:
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37]
谏辞以“是障之也”开头,对厉王“吾能弥谤,乃不敢言”的得意之形首先进行否定。接着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即指出厉王这种做法的不可行性。进而再指出其危害,“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于是提出“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正确解决办法。邵公结合“天子听政”的实际来论,教厉王应当如何做,并指出使民言说对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性。最后又以两个反问质疑否定厉王的这种做法,做到了首尾呼应。因此邵公的这段说辞,篇幅虽小,但内容紧凑有序,逻辑严谨,语言干练,论证充分,且已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已可看作一篇优秀的谏说文了。
又如《烛之武退秦师》中烛之武的语辞:
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38]
在这篇语辞中,烛之武首先有意做空郑国的存在,而全从秦国的角度立论,讲出存郑对于秦的好处,及亡郑给秦带来的弊端。接着指出晋欺秦之事实,挑起秦晋两国间的矛盾,又进一步具体指出亡郑对晋的好处,以及晋才是秦国真正的威胁。可以说这同样是一篇构思精巧、逻辑严密的谏说散文作品。
对于这些卿士大夫的谏说文辞,如今我们将之视为散文。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这些文辞是被视为一篇篇言辞巧妙而理由充分的谏说之辞。这些文辞被世人称道之处,正在于其喻说精巧,构思严密,语辞得当。所有这些全在于卿士大夫个人的创造,是他们个体才华的体现。当这些言辞被史官记下,形诸文本时,对后世卿士大夫、行人便具有典范意义。
二 史官与问对体例的形成
我国有悠久的史官传统,西周时期,史官制度已经相当成熟,并且已有明确的职掌分工。《周礼·春官》中载: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
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
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
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
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39]
足见当时史官之多,分工之细。
到西周中后期时,随着各诸侯国的实力增强,也都相继设置史官,《史记·秦本纪》载:“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40]即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2年),秦国开始设置史官,可以想象先于秦国分封的齐、鲁、晋等国应早已置有史官。《孟子·离娄下》载“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41],也说明了各诸侯国早已有史官对本国史事进行记载。左丘明所编《国语》,是根据各国史料文献“语”汇编而成,其中最早的文献始于周穆王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样能证明,各诸侯国在西周末年多数应设有史官。
通过上文所引《周礼》的有关记载,对于史官的职能,可以得到一个大略的认识,即掌管“典”“法”“书”等官方文献。但对于史官的职掌,我们最熟悉的一点还是记录。《礼记·玉藻》载:“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42]即是说左史主要记录行为事件;右史主要记录言论。《说文》对于“史”的解释也是“记事者也”,突出的都是史官的记录职责。如今我们翻阅《尚书》中的有关篇章,每每会看到,“王曰”“王若曰”“公曰”等,史官实录的痕迹是明显的。同样,阅读《国语》《左传》,王公、君臣间的问对,也比比皆是,余行迈说:“史官记言并非仅限于人君的告誓训令,还包括君臣的对答,公卿大臣的言论,以及盟书(又称载书)、讼辞等。”[43]史官对君臣问对言论的实录,对于我国散文及赋体文学中的问对模式的形成有重要促进作用。
史官虽是对王公、君臣问对言论做记录,是录而不是作,但毕竟是他们将口头言辞形诸文本,若言辞仅停留在口头上,是无从谈论文体的。当史官将君臣问对,行人与诸侯问对及狱讼审讯、辩难等记录下来时,就形成一篇篇问对体例的文本。其中那些问得精、答得巧、说得妙的问对文辞,一旦被史官记录下来,形诸文本,就是一篇篇精美的问对体文辞,尤其是那些诉讼、辩难主题的文辞。战国时期,随着士阶层的崛起,经史官所记流传下来的经典问对文本自然会被士人学习模仿。就纵横策士来讲,他们为推行一己策谋,时常还会模仿君臣问对演练说辞。《战国策》中收录了许多这种虚拟问对之文,如《战国策·魏策一》中《张子仪以秦相魏》载:
张子仪以秦相魏,齐、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谓张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则国家安,而百姓无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计过也。齐、楚攻魏,公必危矣。”张子曰:“然则奈何?”雍沮曰:“请令齐、楚解攻。”雍沮谓齐、楚之君曰:“王亦闻张仪之约秦王乎?曰:‘王若相仪于魏,齐、楚恶仪,必攻魏。魏战而胜,是齐、楚之兵折,而仪固得魏矣;若不胜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国,必割地以赂王。若欲复攻,其敝不足以应秦。’此仪之所以与秦王阴相结也。今仪相魏而攻之,是使仪之计当与秦也,非所以穷仪之道也。”齐、楚之王曰:“善。”乃遽解攻于魏。[44]
相对于史官对王公、君臣问对言辞的实录,这种说辞无疑有了策士主观创作的成分,有策士们的设想在。此外,战国中期以来,庄子、屈原的创作中也多有问对体出现,以此服务于说理、明志。问对体例的写作逐渐被引向文学创作。西汉时期,汉赋作家已能自觉虚设人物问对以进行赋体创作了,如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东方朔《答客难》等。对此,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得很清楚:“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45]
由此,“问对”体例作为一种创作模式,进入了文学创作的实践之中。“问对”体例的兴起与史官对王公、君臣等问对之辞的实录不能说没有关系。
三 史家著述与叙事体、史传体创造
(一)叙事体创造
春秋以来,东周王朝的统治力逐渐衰弱,各诸侯国的实力不断增强,礼乐文化的影响力逐渐下降。诸侯国之间频繁的战争,逐渐检验着人的合理性行为对于国家兴败存亡的重要性,而并非鬼神的庇佑,自身拥有精英文化知识并掌管史记的史官最明此理。但随着周王朝国势的衰微,包括史官在内的精英人士不断出走,陈桐生就指出:“从平王东迁到春秋末年,出于对陵迟没落王朝的不满和失望,东周王朝史官不断上演弃周逃奔的故事。”[46]这种现象使得经典文化不断涌向地方,精英文化下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士阶层的兴起。
到春秋战国之际,称霸兼并战争越发激烈,恃强凌弱的社会现实,列国之间频繁的战争,使礼乐文化、史官文化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然而,这一时期仍旧有一些士人积极倡导礼义仁德,试图恢复宗周礼乐文明,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士人。但在这个时期,结果往往是碰壁。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47]从司马迁的这段叙述中不难看出,孔子“干七十余君”不成后,退而修订《春秋》,仍旧是希望王侯能行“王道”;左丘明因《春秋》而诵史,之后辑成《左氏春秋》[48],以追其意。
严格来说,孔子和左丘明并不是史官,司马迁对左丘明的称谓是“鲁君子”,但因他们与《春秋》《左传》《国语》等带有史书性质的传世文献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史家。这些著作不是官方的,而是缘于个体士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国语》与《左传》中的篇章篇幅相对较长,一方面有对各国史官所记史料的直接引用,其中就包括上文我们所提到的卿士大夫、行人的经典文辞。另一方面编著者本人为记明一个事件的原委,如何巧妙地将他们所见的相关史料编排起来,则又有他自己的构思,当下我们阅读《国语》《左传》中的一些篇目,明显可感其鲜明的故事性、叙事性。再者,有时对一个历史人物,作者对其生平、事迹有较详细的叙述,已开“史传”体文学的先河。而就《左传》《国语》中所呈现出的叙事体文学与史传体文学而言,都可以看作个体士人的创造。
童庆炳曾说:“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要素有三点:即情节(讲什么)—演进(怎么讲)—视角(谁讲)。”[49]童先生所谓的“情节”即是内容,通过一个个事件来叙说故事,但事件之间不能彼此独立,而是要有因果联系;所谓“演进”,即“如何把在某个空间里发生的事件,放到一定的时间秩序中来叙述”;所谓“视角”,即事件、故事由谁来讲。童先生所说的“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三要素,当指文学自觉以后,成熟的叙事文学作品所应当具备的特质。而成书于战国前期的《国语》《左传》中的一些篇章,客观上也已具备这些要素。
《左传》与《国语》相传都是据左丘明讲史所编著,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前期。春秋战国之际战乱频繁、礼乐废弛,传统士人编著史书性质的文献,目的是给君主提供史的借鉴,希望君王行“王道”。因而在《国语》《左传》的篇章中,呈现出明显的道德评判,其标准是“德”“义”“诚”等礼文化下的行为准则。翻阅《国语》《左传》往往会发现,当编著者叙述的一件事或一个人,其性质或行为不合于这些道德准则时,大多会叙述出其结局,而这种结局往往是悲惨的,训诫的目的非常明显。如上文我们所引述《国语》中的《邵公谏厉王弭谤》篇,对于周厉王暴虐且又不听劝谏,结果“三年乃流王于彘”。又如《国语》中的《单襄公论陈必亡》一篇,单襄公受周定王之命,“聘于宋。遂假道于陈,以聘于楚”[50]。进入陈国后,见陈国并没有按月令开展相应的农事工作,且“司里不授馆,国无寄寓,县无施舍”,进入陈国都城后,“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宾不见”,基于种种背时违礼的现象,单襄公回国后,得出陈国必亡的结论,果然,“六年,单子如楚。八年,陈侯杀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陈”[51]。编著者结合史料,把陈国的命运完整地展现出来,其实也是在一次次地重申,不合礼法者,不合礼法之事,必然不会有好的结果。当然偏于记事的《左传》,类似这样的篇章就更多了。
我们想说的是,作者编著《国语》《左传》的目的是给统治者以史的借鉴,敦促其行王道,对于一些王侯违礼背俗的行为,作者都将其悲惨下场、结果列出,这样警示意义更为直接。因为有这样的一种创作目的在,不论这种结果是几年甚至十几年后发生,作者都会有意列出来。如《邵公谏厉王弭谤》,周厉王是“三年乃流王于彘”,《单襄公论陈必亡》中单襄公在周定王六年到楚,而陈为楚所灭是在周定王九年,这里也有三年的时间跨度,显然是编著者自己根据史料加上的,所追求的就是事件的因果效应。这种为了警戒王侯、为统治阶级提供史的借鉴而编排的事件因果联系,与童庆炳先生所认定的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情节”,即事件之间不能彼此独立,要存在因果联系,在客观上是相似的。而且编著者作为战国前期的人,对西周晚期,东周中前期发生的事,以时间为线索进行有序编排,这符合童先生所认定的第二个要素——“演进”。再者,编著者作为局外人,是在讲述前代故事,而不是史官式的实录,并且他们有意追求故事的完整性,表明他们确实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讲述,也同样符合童先生所认定的第三个要素——“视角”。因而作为士阶层的个体,以《左传》《国语》编撰者为代表的史家,在编著诸如《国语》《左传》等历史故事题材的文献时,实则创造出了一种叙事体文学的样式。真正的符合理论规范的叙事体文学虽然产生的时间较晚,但未尝没有对《左传》《国语》中一些篇章的借鉴与仿拟。
(二)史传体创造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说:“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存亡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52]刘勰所论是较为恰切的,左丘明与孔子同时,对《春秋》微言背后的史事是有清晰认识的,于是发微言而为详细事件故事。这在刘勰看来是传体的首创。
传《春秋》者,流传于当下者有三,《公羊传》、《穀梁传》以及《左传》。《公羊》《穀梁》为今文,《左传》为古文。《公羊》《穀梁》为训诂传,《左传》则详于叙述史事。《春秋》中,虽然夫子多以寥寥数语标记历史事件,但所叙事件对于影射礼义之道,警戒君王,皆具有典型性。只是后人或许因无法详知孔子所记事件的原委,不能使其大义灿然,这也是《左传》成书的原因。《孟子·滕文公》篇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53]《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54]并引孔子语“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也可证孔子作《春秋》确实是“见之于行事”,即以鲜活事例影射道义与兴亡之理。司马迁所指出的“弑君” “亡国”“诸侯奔走”无一不是警醒王公世人的大事。
左氏将《春秋》史事具体化、详细化,展开记叙,追求事件的完整性,客观上开启了“史传”体的先河。刘勰说:“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55]即是说传就是转,转受经旨大义于后人,是经书的辅助性读物,又是记事书籍中的翘楚。刘勰指出《左传》是为转受《春秋》大义于后人,是史传体文学的先河。但又说《左传》是记事书籍中的翘楚,则又有承认其独立存在的一面。蒋伯潜说“《公羊》《穀梁》为‘传’之正体;《左传》则是‘史传’”[56],因此,若抛开《左传》和《春秋》的关系不论,单看《左传》,其中对于历史事件、对于历史人物事迹的完整性叙述,实则为以后历史类文献的编著写作提供了范例,对传记体文章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四 庄子“寓言”体创造
战国以来,随着士阶层的兴起、壮大,思想文化层面呈现出我们所熟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士阶层自身的历史责任感、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也是士人个体自我意识的体现。孟子曾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57]他们著书讲学,宣扬一己之学说,都非常主动、自觉。这不但丰富了先秦文献,也丰富了先秦文体类别。从文学文体的视角看,这一时期具有创造之功,且对后世文体影响较大者,是庄子和屈原。
阅读《庄子》,我们能感觉到其论说的宏大,思想的深邃,以及语言的汪洋恣肆,作为我国早期文学形态,其首先具有典型的风格学意义。同时也要注意,庄子说理,多是以人物问对形式展开,这在问对体的发展脉络上,是重要的一环。从《寓言》篇和《天下》篇的相关记载看,这是庄子有意为之。庄子设置人物问对,客观上使其哲理、学说通过他人(物)之口讲出,而这正是其想要的阐释方式。《寓言》篇中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58]所谓“藉外论之”,就是借助他人之口来说话,因为这样能更容易让别人信服,即“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这足以证明“寓言”是庄子有意为之。借助他人之口来说话、说理,这一创作体例被学者们称为“寓言体”。如《庄子·渔父》篇中,即是主要借助渔父和孔子的对话,让渔父指出孔子“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59],设置孔子卑躬地询问,让渔父讲出真与道,最后又通过孔子之口表达出对“道”的敬佩。
《庄子》中,作者设为问对以说理,其中有将历史人物虚化、艺术化的现象,与事实中的历史人物本身的性格特征存在一定差距,这时历史人物成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完全服务于作者说理,最明显的是孔子形象,《庄子》中所出现的孔子形象,与《论语》及史书中所记载的孔子形象,出入非常大。这比《战国策》中策士们在推演人物问对时所作之文辞,更接近文学创作。《战国策》中的假设人物问对之辞,有从现实人物身份、性格特征考虑的一面,策士们会从王侯实际的性格出发,想象他们会怎样问,而“我”又怎样对,因而这种推演假设有合乎现实的一面。庄子与此不同,《庄子》中所假设的人物问对,更接近创作手法,与现实人物存在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其中有作者的艺术构思与想象在,是一种创作。因此,“藉外论之”的寓言体可以看作庄子的创造。
五 屈原的“体由独创,语出新裁”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创作了以《离骚》为代表的一系列优秀作品。在屈原《离骚》等作品之前,虽有《诗三百》篇,但从文本体式上说,并没有同《离骚》《九章》等相类似的篇章存在,这本身就是一种文体的创造,如刘勰就说屈原是“自铸伟辞”,明人张京元认为是“体由独创,语出新裁”。当然屈原作品的文体样式并不是等齐划一的,一些学者统称之为“楚辞”体或“骚”体,实则抹杀了其文体的多样性、丰富性。如同为诗体,《离骚》与《天问》在文本特征上就有明显的不同;《九章》之中《橘颂》与其他各篇也不相同;《招魂》《卜居》《渔父》显然又不属于诗体。学者们所说的“楚辞”体、“骚”体,其实更多的指向了《离骚》的文体样式,而且称之为“楚辞”体或“骚”体,在称谓上也没有表现出《离骚》的体式或内容功能等特征。就称谓上讲也是模糊笼统的。屈原能够创作出不同类别的文体,表明他已具有一定的文体意识及相应的文体功能意识。这也是本书所要着重阐述的。
综观以上所论,春秋以降,随着经典文化的下移,士阶层开始兴起,他们或是著书立说积极入世,或是倡导自然,遗世而独立,也有如屈原这般“发愤以抒情”者。在说理、献策、抒情的过程中,创作了大量文辞,这些文辞因作者创作目的、创作需要的不同而体式各异。相对于仪式礼制下的文体创造,这些创作极富个体色彩,多是“因情而立体”,即根据一己的表达需要而确立文体样式,与仪式制度下的文体创造表现出极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