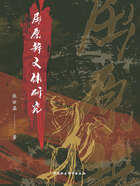
第一节 仪礼制度与文体生成
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催生了记事符号——文字。文字成熟后,作为语言文字集合体的文体,其生成的直接原因是某种具体仪式、礼制的需要。从夏商巫术仪式到西周礼乐制度,不同性质、样式的仪式制度决定了不同文本体式的生成,决定了文体各自不同的功能,也决定了文体最初的体征与分类。祭歌、颂、誓、诰、盟等文体的生成鲜明地体现着这一点。
一 巫祭仪式与祭歌生成
在文字没有产生的远古时期,人类对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事件不会有太久的记忆,为满足记事的需要,文字起初以一种记事图像符号的形式出现。当人们需要完整记录一次较重大活动,把许多符号串联在一起时,便形成了一个文本,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一种文体了。目前,我国最早的成熟文字是甲骨文,是锲刻在龟甲、兽骨上的一种文字,主要是记录当时占卜仪式活动的内容。夏商文化的主体形态是巫文化,祭祀、占卜等巫术活动是世人生活中重要的仪式活动,而每次占卜后,会将有关占卜的诸种事宜刻于相应的卜甲、卜骨上,包括占卜时间、占卜者的名字、占卜的内容及占卜后的应验情况。作为记录占卜的需要,甲骨文本的生成正是占卜仪式活动的产物,它属于占卜活动的一部分,承载着记录占卜活动的功能,所以也称为甲骨卜辞,突出的正是它与占卜仪式活动的密切关系。可以说人类生活发展的需要催生了记事符号——文字。而作为语言文字集合体的篇章文体,其生成的直接原因,则是人类某种具体仪式礼制的需要。
上古最主要的巫术仪式是祭祀,这是人类各民族发展史上都会经历的文化阶段。根据传世典籍的记载来看,部落首领、酋长乃至国家形成后的君王,他们都拥有另一个身份——巫。李泽厚先生指出,“尽管有各种专职的巫史卜祝,最终也最重要的,仍是由政治领袖的‘王’作为最大的‘巫’,来沟通神界与人世,以最终做出决断,指导行动”[1]。《国语·楚语下》载:“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2]颛顼帝“绝地天通”后,集巫权于一身即属于这种情况。
《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3]《山海经·大荒西经》载:“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4]这能证明夏启的大巫身份。商王汤也有“以身祷于桑林”的故事。《吕氏春秋·顺民》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5]《淮南子·主术训》也载:“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6]这足可证明商汤的大巫身份。
夏启“大乐之野”与商汤“身祷桑林”指的都是祭祀仪式活动,而在这样浩大的巫祭活动中往往会伴有歌、乐、舞蹈。《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7]屈原在他的作品中对此也有提及。《离骚》中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8]《天问》说得更为具体,“启棘宾商,《九辩》《九歌》”[9]。因为时代久远,《九辩》和《九歌》虽已被传说为天乐,但实际应是夏启于天穆之野为祭祀上帝而作的乐歌,屈原所谓“夏康娱以自纵”,则说明了为娱神的需要,这套乐舞充斥着原始性爱色彩。据此可证明原始社会早期因巫祭仪式活动的需要确实创制产生了一批祭祀乐歌。
屈原自己也作有《九歌》,同样与祭祀活动有联系。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歌序》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10]从王逸的这则序文中,可以得到三点认识:首先楚国沅湘间有信鬼好祠的风俗,这与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对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的描述相符;其次,“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句,则明确指出,为了祭祀仪式活动中娱神的需要,他们会创作歌、乐、舞;再次,屈原见闻了南楚之人为祭祀仪式而创作的歌辞,因其“鄙陋”,为此而改作《九歌》。现在一些学者也指出,夏启《九歌》与楚《九歌》间具有直接的关系,如潘啸龙通过考证夏启的《九辩》和《九歌》的“天穆之野”与楚“沅湘之间”地理位置上的相合,认为“‘沅湘之间’流传的《九歌》,原来就是传说中的夏启《九歌》”[11]。黄灵庚根据上博简《容成氏》所载汤攻夏桀,夏桀逃跑“去之苍梧之野”,认定夏桀到过苍梧之野,“这样,夏后氏颂祖祭天的《九歌》,随着夏桀王朝的南移,最终流传到了江南、沅、湘流域及其苍梧地区”[12],屈原于沅湘间所见《九歌》即是民间化了的夏启《九歌》。潘、黄两位先生都论述到了夏《九歌》曾流传到楚地的事实。此若准,则可进一步证明在巫祭仪式活动中,确实创作保留下来了一些祭歌。因为屈原《九歌》与夏《九歌》的这层关系,使我们对祭歌的生成、功用有更为直观的认识,即最初的祭歌因巫祭仪式的需要而作,承担娱神的功能。
因为所作的祭歌要在祭祀仪式中合乐演唱,所以客观上就要求这种文辞必须整齐、有节奏、合律动,夏启《九歌》的文本我们已不可能看到,但从屈原《九歌》中可窥一斑,如《东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
可见叹词“兮”在中间掌控着演唱节奏,以合乎音乐的节律。由此又能证明仪式不但决定文体的生成,而且仪式的性质、样式同时又决定了文体最初的体征。
二 “告成”仪式与颂体生成
《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时间跨度达五百余年,从诗篇来源上看,有王公贵族的创作,有士大夫的讽谏之作,也有采诗官的采诗、瞽矇献诗。对于大部分诗篇来说,并不好把握其原初文本的具体生成背景,但可以肯定的是,也必然和一定的活动事件相关联,或因事而作,或为事而作,其中颂诗部分的创作与“告成”仪式关系密切。《诗大序》载:“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13]“成功”指武王伐殷成功,周人成功享有天下;颂,即容,即是以诗乐舞的形式将成功伐殷、平定天下的过程,象征性地表演给先祖先王,以达到告知先王的目的,其中最突出的是舞,《释名·释言语》载:“颂,容也。叙说其成功之形容也。”[14]容,即是舞容。《逸周书·世俘解》对此有较为具体的记载,“甲寅,谒我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15]。“谒”是告诉,“我”为“戎”之讹。即甲寅这一天,武王带赤旂白旂,在殷地临时建起的宗庙前向先祖先王禀告了牧野成功伐殷之事,籥人演奏《武》乐,跳《万》舞,象征性地将伐殷胜利的过程演绎于先祖先王庙前。之后周公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完整的《大武》乐章,《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楚庄王语,便提及《大武》乐章及其用诗情况。
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16]
楚庄王所引“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耆定尔功”“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绥万邦,屡丰年”诗句,均见于《诗经·周颂》,分别在《时迈》《武》《赉》《桓》篇中。因楚庄王提及《武》,又说“其三”“其六”,可以断定《武》《赉》《桓》属于《大武》乐章中的三成,这正好能够证明颂诗的生成与祭祖仪式活动的密切关系。由此可知,颂诗,即是为祭祀先祖仪式而创作,并配合乐舞表演。《礼记·乐记》载孔子答宾牟贾之问,就详细说到了《大武》乐章的舞容,“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17]。因此可以断定,颂诗的生成有其特定仪式背景,最初是为祭祖“告成”而作。
因为颂诗也要伴乐演唱,所以客观上也同样要求其语言要齐整;因为“告成”的主要形式是武舞,因而颂诗的体式不会如西方叙事史诗那样长。可见颂诗最初的文本体征也被仪式的形式决定了。
三 誓师仪式、训诰仪式与誓、诰生成
《尚书》是我国成书最早的文献典籍之一,对于其中《虞夏书》《商书》的写定时间,学界尚存在争议,但《周书》中一些篇章的写定时间是能够确定的。学界普遍认为《牧誓》《大诰》《康诰》《梓材》《多士》等作于西周初年;《费誓》《文侯之命》《秦誓》等作于东周前期。就文体而论,这些篇章至少存在两种文体类别,即誓与诰,它们的生成也均与相应的仪式制度有关。《书序》载“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18],“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19],“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20]。此外,《史记·周本纪》中也有关于《牧誓》《大诰》等篇章创作背景的记载。这些记载既介绍了篇章的创作时间,又交代了创作场合、缘由。
从宏观上讲,这些篇章映射出宗周王朝打天下与治天下的历程;反向观之,也恰恰证明,诸如誓、诰等文体的产生也确实与国家这些重大活动有直接紧密的联系。具体来说,誓是誓师仪式活动的产物,在文王、武王为统一天下所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中,需要举行必要的誓师仪式,以激励将士。《史记·周本纪》中对牧野之战前夕的誓师仪式有非常详细的记载,“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 、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21]。根据这段记载来看,誓,本是战前君王举行的一种训话仪式,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所持这些物件皆具有一定宗教象征意义,韩兆琦先生认为“左手杖钺,示有事于诛;右手把旄,示有事于教令”[22]。这时将士被要求“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做出一种战前激昂紧张的姿态,然后君王训话,“誓已”,即誓师仪式结束后,便“陈师牧野”,做好了战前军队的部署准备。这一仪式的程序是简明的,其中仪式的核心是君王对将士的训誓,那么自然君王首领训话的言辞会被称为誓辞,史官或整理者在给这些言辞命篇时,也必然会以誓命篇。吴承学认为“对篇章的命名,也是文体认定与命体的前提,所以命篇是文章学与文体学发生的基础”[23]。那么对于这些以“誓”命篇的篇章而言,后世在判定它们的文体类别时,因其有特定的生成环境,有特定的功能,有指示这种生成背景的篇名在,后人以“誓”命体,便顺理成章了。
、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21]。根据这段记载来看,誓,本是战前君王举行的一种训话仪式,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所持这些物件皆具有一定宗教象征意义,韩兆琦先生认为“左手杖钺,示有事于诛;右手把旄,示有事于教令”[22]。这时将士被要求“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做出一种战前激昂紧张的姿态,然后君王训话,“誓已”,即誓师仪式结束后,便“陈师牧野”,做好了战前军队的部署准备。这一仪式的程序是简明的,其中仪式的核心是君王对将士的训誓,那么自然君王首领训话的言辞会被称为誓辞,史官或整理者在给这些言辞命篇时,也必然会以誓命篇。吴承学认为“对篇章的命名,也是文体认定与命体的前提,所以命篇是文章学与文体学发生的基础”[23]。那么对于这些以“誓”命篇的篇章而言,后世在判定它们的文体类别时,因其有特定的生成环境,有特定的功能,有指示这种生成背景的篇名在,后人以“誓”命体,便顺理成章了。
因为“誓”是君王对将士的训话,是现场演说,不是歌唱,所以其文辞长短不一,表现出明显的口语化、散体化特征。如《史记·周本纪》所载武王在牧野之战前的誓辞:
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今予发维共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不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罴,如豺如离,商郊,不御克犇,以役西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24]
因为要与敌方战斗,所以誓辞必然会说自己是正义、合天意的,并且罗列对方的罪行,这成为誓辞固定的基本内容及体例。而且不断给将士鼓气,“勉哉夫子”,要其尽力。可见誓这种文体,不论是其体征还是内容,最初也都鲜明地决定于其仪式性质。
西周克殷之后,周王朝面临治天下的问题,安抚殷商遗民、分封以及处理好天人关系等,西周初期的文献鲜明地反映着统治者的这一系列活动。《史记·周本纪》载,起初武王“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不久,武王去世,“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尚书》中有《大诰》篇,结合其内容看,应作于管、蔡叛乱之后,周公讨伐他们之前。这篇诰辞是周成王的口吻,应是周公以成王的口吻而作。从文本内容看,“王若曰:‘猷!大诰尔多方,越尔御事’”,“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显然是“王”面对邦国之君臣所诰,当发生在一定的场所,类似于今天的会议,但其核心主题无疑还是体现君王行为的诰及诰之内容,因而就这篇文辞讲,之后的命篇及命体,自然也都会以“诰”命之。可以说不论是誓还是诰,其生成都有它们一定的背景,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特定仪式活动的产物。
四 盟誓制度与盟的生成
周公“制礼作乐”后,中原文化逐步进入理性阶段,国家各项活动也趋向规范化、制度化,有了可资遵循的“礼”。从《仪礼》《周礼》等典籍的记载中,可见西周精密的制度规范。而与此相应,我国古代文体的生成也进入主要受礼制决定的时期。
周代史官制度发达,记录并创作了大量的与之相应的文体。《周礼·女史》载:“女史掌王后之礼职,掌内治之贰,以诏后治内政。”[25]《周礼·大祝》载:“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26]《周礼·内史》载:“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27]据此可知,史官创作、记录了大量礼制活动下的各种辞令,这说明西周时期,不同礼制仪式下,生成了许多不同的文体类别,只是由于时代久远、战争、文字载体腐朽等,这些文献并没有保留下来多少。因而当下我们所见西周时期的文献不多,对于一些诸如会盟仪式等活动的具体情境及所创作的具体文辞,也无从知晓。
进入春秋时期,因《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的记载保存,使得我们对这一时代的礼制活动及其与之相应的篇章文体的生成,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比如会盟制度与盟辞的生成。翻阅《左传》可以找见大量有关盟誓活动的记载,如《左传·成公十二年》所记载的晋楚之盟:
宋华元克合晋、楚之成,夏五月,晋士爕会楚公子罢、许偃。癸亥,盟于宋西门之外,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28]
这段有关晋楚之盟的记述,交代了盟誓的时间、地点及所作之盟辞。又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29]同样也交代了盟誓的时间、地点和盟辞。当然,这些只是结盟仪式过程中的一部分,并不完整。《礼记·曲礼下》对“涖牲曰‘盟’”的注疏载:“盟之为法:先凿地为方坎,杀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盘,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为盟。书成,乃歃血而读书。”[30]这里对盟誓过程的解说是非常详细的。陈梦家先生根据《左传》,并结合出土文献,对春秋时期的盟誓制度做过翔实的考察,他认为春秋时期的盟誓程序主要有十项,顺序为“为载书”、凿地为“坎”、“用牲”、盟主“执牛耳”、“歃血”、“昭大神”、“读书”、“加书”、“坎用牲埋书”、载书之副“藏于盟府”[31],可见“为载书”是盟誓仪式活动首先要做的,所谓“载书”就是盟辞,《周礼·司盟》注云:“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32]载书一般为一辞数本,如孙诒让云:“盖凡盟书,皆为数本,一本埋于坎,盟者各以一本归,而盟官复书其辞而藏之。”[33]上文我们所引成公十二年晋楚之盟“凡晋、楚无相加戎……无克胙国”,即是载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现于侯马的书于石片上的载书,则以实物的形式证明了盟辞的存在,并有其独立性。因而可以这么说,正是有盟誓仪式制度的存在,才促成了盟辞这种文体。
因盟书是要宣读的,所以这就决定了其文辞的口语化特征;因为仪式的目的是约信,所以盟辞必然包含盟誓各方要遵守什么,而若违背盟言,又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因而盟书的最后部分便固定为诅辞。上文我们所引盟辞鲜明地体现着这些特征。这也可证明仪式本身的规定性最初也决定了文体所具有的体征及其内容。
综观以上所论,上古以来至春秋,流传于今的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文体类别,它们的产生都与相应的巫祭仪式、礼仪制度有直接关系,是人们践行这些巫祭礼仪、仪式制度的直接产物。从夏商巫文化中的巫祭占卜仪式,到周初巫礼并存下的颂祭仪式,再到“制礼作乐”后具体制度下的仪式。不同性质样式的仪式、制度促成了不同文体的生成,决定了文体各自不同的功能,也决定了文体最初的体征。因为这些文体是在不同的仪式制度中生成的,所以文体内容本身鲜明体现着相应仪式制度的内容和要求,各文体也必然会承担各自不同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