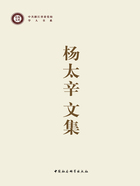
一 《荀子》与《乾文言》
《文言》是解释《易经》大义的“十翼”之一,分别阐释乾坤两卦的象征意义,故又可分称《乾文言》和《坤文言》。乾卦取象于天,其意为健;乾爻取象为龙,意在表现乾健之因时变化。《乾文言》结合天道人事,充分阐发了乾健的内涵及其变化过程。《荀子》则重在人事,把《乾文言》及《乾彖》、《乾象》所阐发的阳刚至健精神用之于治国之道和君子修养。
(一)乾之“四德”与荀子的思想体系
为了顺时应人,齐一天下,荀子构建了一个以礼义为中心、以仁知为至极的人治、礼治、法治、术治统一的思想理论体系。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建立大一统的封建主义国家的系统理论和完整方略。这个体系的理论基石是乾之“四德”——仁、礼、义、知;其精神支柱为乾之阳刚至健和自强不息。
《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元亨利贞”,原是贞卜之辞。《乾文言》根据春秋以来的流行观念,把它解释成乾健流行的四个层次:于天道为春、夏、秋、冬;于人道为仁、义、礼、知,要求君子体仁、合礼、和义、正固。荀子则以此为依据,建立起了他的以礼义为中心、以仁知为至极的思想体系。《乾文言》关于“四德”的观念及命题在荀子思想中体现和展开如下:
体仁:“体仁足以长人”,《文言》以“体仁”作为掌政治人的首要条件。荀重礼义,孟重仁义,这已成为常识。然荀子虽重礼义,同样以仁为体,以礼为用。其证:1.他以仁为王者以至诸侯、士大夫的必备条件,即认为外王必以内圣为先:“人主仁心设焉,知其役也,礼其尽也。故王者先仁而后礼,天施然也”(《大略》);“故仁人在上,……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荣辱》)。荀子虽说过积礼义者可以为君子,然曰圣曰王则非仁不行,“礼之生,为贤人以下至于庶民,非为成圣也”(《大略》)。为圣人则非体仁无遗不可,“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闵,明达用天地理万变而不疑……仁知之极也,夫是之谓圣人审之礼也”(《君道》)。2.以仁为礼之本,礼为仁之经。如:“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劝学》)。3.他序列诸德,常以仁为首。如:“仁义礼乐,其致一也”;“仁义礼善之于人也,辟之若货财粟米之于家也”(《大略》);“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性恶》)。荀子推演《文言》“体仁足以长人”之意,以仁心为治国之本,以礼义为仁义之径,以仁为首德,以仁知为至极,丝毫没有忽视内圣之迹象。自宋明理学家至海外新儒家,皆认为荀子轻内圣而重外王,不知何据?
合礼:荀子以体仁为内圣,又以合礼为外王,对“嘉美足以合礼”中的“合礼”两字体悟甚深。他把礼之用推及于人生修养、社会事务、国家政治等一切领域,提出“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强国》);“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修身》)。这也就是人生事业、天下国家一切皆须合礼:对人来说,举凡血气、志意、思虑、食饮、居处、动静、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皆须由礼来调节(《修身》);对事来说,只有任其责者“其言有类,其行有礼”,才能“举事无悔”和“应变曲当”(《儒效》);对国家来说,只有“修礼以齐朝”,才能“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然后节奏齐于朝,百事齐于官,众庶亲于下”(《富国》);对天下来说,其统一之径,非礼莫行,只有“推礼义之统”,才能“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不苟》)为了使天下国家和君子士庶更好地合乎礼义的规范,他突出了礼的作用,丰富了礼的内涵,这早已为世人所公认。
和义:对“利物足以和义”的涵义,孔颖达《周易正义》说:“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其宜,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何妥曰:“利者,裁成也,君子体此利以利物,足以合于五常之义。”综合两家之说,《文言》这个命题包含着裁成万物使之各得其宜即义的意思。荀子利物,主张“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王制》)。但是,生物靠天,成物靠人,荀子称之为“天生人成”。他认为要物尽其美,必须人尽其分;要人尽其责,士大夫以上要“位必称禄,禄必称用”,对下则须“裕民以政”,生民富民,这就需要和之以义。“若是则万物各得其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如山丘,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富国》)。荀子义利观的特色是,在利物的基础上言义,在礼义的制约下言利。他主张以义制利,以利和义。这既不同于孟子的曰仁义而不曰利,也不同于墨子的以利为义。其中尤为卓绝的是,他利物是为利民,要求“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使得“民不困财”。这就是说君子利物是为和义,自身则应以“公义胜私欲”(《修身》),“欲利而不为所非”(《不苟》)。荀子的义利观是《乾文言》的“利物足以和义”的具体而微的发挥。
贞固:“贞固足以干事”,意为正固是处事的根本。荀学为儒学的实践形态,以通过“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非十二子》),去建立“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为己务(《儒效》)。为了完成这个事业,必须具有贞固的德操。因此,荀子屡言:君子应“执神而固”,“万物莫足以倾之之谓固”,“神固之谓圣人”(《儒效》)。他以“神固”为德操;君子“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劝学》)。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荀子曰生死由是,其正固的精神一致,然着重点有所不同,孔重仁恕,孟重仁义,荀重仁知。孔颖达《周易正义》说:“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谓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为之干”,以知配贞。这样,乾之四德依次为仁、礼、义、知,与荀子之以礼义为中心,仁知为至极的思想恰契合无间。
(二)乾之“六龙”变化和荀子的君子之道
《易经》善于“随其事而取象”,大概因传说中的龙刚健而善变,故取为爻象以喻乾阳之变化。《文言》解易,以龙之潜、见、惕、跃、飞、亢,说明阳气之潜藏升降,君子之出处进退,天道人事兼及。《乾文言》在阐释乾卦各爻时提出的一些范畴和命题,在《荀子》中几乎皆有回应,试揭载如下:
1.《乾文言》曰:“初九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潜龙,喻处于自修阶段的君子。《乾文言》认为在此阶段的君子应潜心自修,遯世无闷。荀子通过称赞古之处士和今之诚君子,畅说此意:“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悱,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非十二子》)。其中“不诱于誉,不恐于悱”,即“不成乎名”;“不为物倾侧”,即“不易乎世”。
2.《乾文言》曰:“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见龙,喻刚离隐见世而尚未升腾飞跃之君子。君子在这时,特别要言行信谨,防邪存诚,善而不夸,德而广化。荀子主积极用世,倡潜隐是为了更好地显于世。因此,对《乾文言》倡导的君子应正行中道之理,畅加推演。《不苟》曰:“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若是可谓悫士矣。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不但与《文言》“庸言之信,庸行之谨”语同意合,而且从反面引申发挥,以言行是否信谨,作为君子小人之别。《修身》说:“君子隆师而亲友,以致恶其贼,好善无厌,受谏而能诫”。《不苟》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这与《文言》的“闲邪存其诚”的思想是一致的。特别应引起我们重视的是荀子提出致诚之道,在于“慎独”:“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以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操而得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不苟》)。《大学》、《中庸》之“慎独”一词,不见于《孟子》,盖出于荀子,亦未可知。荀子说:“功虽大,无伐德之色,省求多功,受敬不倦”(《仲尼》);“仁义在身而色不伐”(《哀公》),这是《文言》“善世而不伐”的进一步的发挥。
3.《乾文言》曰:“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 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
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 ,虽危无咎矣。”
,虽危无咎矣。”
 龙,喻处于危惧之地的君子。这时,君子应加紧进德修业,不骄不忧。《乾文言》对君子应如何进德修业所列的要求,均为荀子接受和发扬。如他认为君子应“忠信以为质,端悫以为统”(臣道》);“故为人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强国》)。荀子论修辞,以端诚为先。他的“谈说之术”,首先是“矜庄以蒞之,端诚以处之”(《非相》);“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正名》)。他对言不由衷的巧言诡辨,奇辞怪说,则深恶痛绝。这些论述很显然是对《文言》的“忠信所以进德”、“修辞立其诚”等思想的发挥。此外《文言》的修业应“知至”、“知终”的主张也为荀子所继承,他认为治学既要“真积力久”,“全粹尽美”,又要“学数有终”,“终于读礼”(《劝学》)。
龙,喻处于危惧之地的君子。这时,君子应加紧进德修业,不骄不忧。《乾文言》对君子应如何进德修业所列的要求,均为荀子接受和发扬。如他认为君子应“忠信以为质,端悫以为统”(臣道》);“故为人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强国》)。荀子论修辞,以端诚为先。他的“谈说之术”,首先是“矜庄以蒞之,端诚以处之”(《非相》);“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正名》)。他对言不由衷的巧言诡辨,奇辞怪说,则深恶痛绝。这些论述很显然是对《文言》的“忠信所以进德”、“修辞立其诚”等思想的发挥。此外《文言》的修业应“知至”、“知终”的主张也为荀子所继承,他认为治学既要“真积力久”,“全粹尽美”,又要“学数有终”,“终于读礼”(《劝学》)。
4.《乾文言》曰:“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跃龙,喻君子处于可上可下之位,或跃进上升,或退处下位,这是由于世事无常,并非出于自己的邪念,也非脱离群众。然而,无论升降进退,君子都要抓住时机,加紧进德修业,方可无过。荀子深明《乾文言》释此爻之意,他引申为:君子“见由(被重用)则恭而止,见闭(被阻塞)则敬而齐;喜则和而治,忧则静而理;通则文而明,穷则约而详”,并以此与小人之“见由则兑而倨,见闭则恐而险”的种种表现对比,以详明此理(《不苟》)。
5.《乾文言》曰:“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覩。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飞龙,喻君子有君德又有君位,天下声气相应,同类相从,莫不从善而化。荀子善用其意而不泥于所谓君德君位,大其堂庑而拓展其用,激励士君子“慎其所立”,鸣求友声,自强不息,以成大业。他在《劝学》、《大略》、《不苟》等篇中反复申明此意,概言之曰:“君子絜其身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故马鸣而马应,牛鸣而牛应之……谁能以己之潐潐(洁白)受人之掝掝(污黑)者哉”(《不苟》)。
6.《乾文言》曰:“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上九,居乾卦之极,物盛必衰,阳刚也不例外。《文言》指出高居众上的君子,其失是“无位”、“无民”和“无辅”,只要知悔而改,“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仍可穷通变久,持盈保泰。《荀子》之终篇《尧问》,借历史人物和传说故事,钩深致远,显微阐幽,充分发挥了亢龙有悔而无咎趋吉的易理。如尧问于舜而知“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倦,而天下自来”;周公知礼贤下士,于千百人中得三士,“以正吾身,以定天下”;魏武侯闻吴起之“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莫己若者亡”之言,逡巡再拜,改自满之过;楚相孙叔敖,“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禄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礼愈恭”,因此,“不得罪于楚之士民”。这些故事,形象地指引天子、诸侯、卿相等身居高位者,解决“无辅”、“无民”的问题,与《文言》交相彰明“亢龙有悔”之理。总之,荀子倡导的君子之道渊源于《乾文言》的“六龙”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