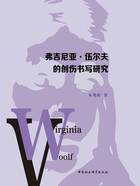
第三节 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及研究价值
一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鉴于上述伍尔夫心理分析研究现状,笔者在本论文研究中,选取心理创伤学视角,依据心理创伤理论,主要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研究伍尔夫及其作品,寻找伍尔夫所受的精神创伤与文学创作的对应关系,探讨其创伤书写的作用与功效。
创伤,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在20世纪的人类历史上,现代性暴力更是广泛地渗透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领域,人们不堪重负,伤痕累累。有人说,20世纪是创伤的世纪,把20世纪的文化也相应地称为“后创伤文化”(post-traumatic culture),创伤被用于界定一切、解释一切。目前,创伤已从个体心理疾病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症候,从临床医学现象演变为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从医学、精神病临床实践转向了文学、历史、哲学和文化研究等人文领域,从病理学概念扩展为流行的公共政治、学术话语和研究范式。在数次转变中,创伤的研究范围日益广泛,创伤的理论探讨日趋深入和系统。创伤与再现、创伤记忆与历史叙事、创伤与治疗、创伤与文学表达等关系问题成为学界研究和争论的焦点。其中,有关创伤与治疗的理论研究在近二十多年来更可谓多姿多彩,尤其引人注意。
基于本研究的需要,我们择取创伤的定义、创伤与复原、写作与疗伤这三个问题进行梳理、论述和探讨。
(一)创伤的定义
创伤(trauma),原初意义为外部力量所导致的生理、身体损伤,19世纪晚期,获得了精神、心理伤害的含义。因而,它既是一个病理学术语,也是一个心理分析学术语。本文所用的“创伤”,指精神创伤或心理创伤。
19世纪末,创伤研究早期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精神病医生、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和当时杰出的内科医生皮埃尔·贾内(Pierre Janet)以发生在女性身上的身心失调症,即“歇斯底里”为基础,对创伤进行了研究。
贾内指出,自我意识是心理健康的核心因素。个人对自己过去的记忆,伴随着对现时的敏锐感知,决定了个人能否对外界压力作出恰当反应。他使用“潜意识”一词来描述记忆的集合,认为对过去经验留下的记忆进行分类、整合有助于人们应对随之而来的挑战。然而,当人们经历创伤事件时,会产生激烈的情绪反应,现有的心灵认知结构往往无法适应所遭受的恐惧体验。这样,创伤记忆游离于意识和自发控制之外。当病人无法将创伤体验整合到整体意识中时,就会“固着”于创伤,这种附着会侵蚀病人的心理能量。它们“虽然越出了意识,但是仍存留在受创伤者的观念范围中,并以某种再现伤害片段的方式(诸如视觉意象、情绪条件、行为重演)继续对他或她的思想、心境和行为施加影响”。[9]
弗洛伊德认为“固着”就是过去经验,尤其是孩提时期的性经验形成的潜意识幻想,创伤发生时的“固着”是创伤性神经症的病源之所在,并且认为,“这些患者在其梦中时常重复这种创伤情境;而对于那些可以分析的癔症来说,似乎其发作就是完全召回这个创伤的情境,好像这些患者没有完成这个创伤的情境一样,好像他们仍然面对着某种没有处理好的任务一样;……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心理过程的所谓的‘经济’的观点”[10]。在此基础上,他阐述了关于创伤的完整观点:“‘创伤’一词只具有经济意义。某种经验如果在短时期内,给大脑提供强有力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应付或适应,从而使大脑能量的分配方式受到永久的干扰,我们把这种经验称为创伤经验。”[11]虽然并非每一种创伤的“固着”都会导致神经症,但受害人总是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中,不能正视现实,无法走向新生,也是可能的情况,“一个人因遭遇到创伤事件而完全动摇了其生活的基础,他放弃了对现在和将来的所有兴趣,并毅然永久地沉迷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12]。
贾内和弗洛伊德都强调了导致创伤事件的高度刺激性和突如其来性、心灵的无力应对和无法适应性、创伤经验的重复再现性,这些论述为当代学界理解创伤、阐释创伤奠定了基石。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1994年颁布的《精神紊乱的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作出了界定:“在受到一种极端的创伤性刺激后连续出现的具有典型性特征的症状[13]。”2000年,该协会在《心理障碍诊断与分类手册》(第四版,修订版)中,将PTSD的症状分为三大类:创伤事件的再体验,对创伤相关刺激的回避和一般反应的麻木感,以及持续的高唤醒状态。并且对创伤作出了专门的定义:“个人直接经历一个涉及死亡,或死亡威胁,或其他危及身体完整性的事件,或目击他人涉及死亡、死亡威胁,或危及身体完整性的一个事件;或经历家庭成员或其他亲密关系者预期之外的或暴力的死亡、严重伤害,或死亡威胁或损害(标准A1)。此人对该事件的反应必须包括强烈的害怕、无助感和恐惧(儿童的表现可能是行为紊乱或激越)(标准A2)。”[14]
世界卫生组织于1992年出版的《国际疾病分类标准》(Interna 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ICD-10)对创伤后应激障碍也有明确的定义和症状诊断标准:“这是对一种(短暂或长期的)具有异乎寻常的威胁性或灾难性应激事件或情境发生的延迟或延长性反应。……典型特征包括在侵入记忆(‘闪回’)、睡梦或噩梦中反复再现创伤场面,在‘麻木’感和情感迟钝的背景下发生与他人疏远、对周围环境淡漠无反应、快感缺失以及回避易使人联想起创伤的活动和情境。常有自主神经过度兴奋伴有过度警觉,一种增强的惊跳反应和失眠。”[15]并且将精神创伤及其范围表述为:“某种由非同寻常的威胁或灾难性事件所引发的精神紧张状态……包括自然灾害、人际争斗、严重的外伤、目睹他人死亡或本身被折磨,以及恐怖、暴力或其他犯罪行为的受害者。”[16]
哈佛大学著名精神病学教授朱迪思·赫尔曼(Judith Herman)这样描述创伤:
心理创伤是一种自己感觉很无力的苦痛。在创伤中,受害人由于受到强力冲击,处于无助状态。如果这种强大的力量来自于人,我们称之为暴行。创伤事件的破坏性往往超出了受害人正常的自我心理防御机制,使受害人失去正常的自我控制、与人相处以及理解事务的能力……创伤事件之所以异常,不在于它不常见,而是因为它超出了人们正常的生活适应能力。与普通的不幸事件相比,创伤事件一般会威胁到人的生命安全或身体的健全,或者会使人与暴力和死亡相遇。《精神病学综合教程》中说,心理创伤的普遍特征是极度恐惧、无助、失控和灭亡感。[17]
中华医学会对PTSD作出如此判定:
经历过严重的创伤[性]事件并具有以下的特征性症状持续一个月以上者:一是重新体验创伤[性]事件(包括梦境中重现全部或部分)。二是回避与事件有关的任何刺激并出现广泛的麻木反应(表现为感觉麻木,情绪麻痹)。三是多种形式的情绪性及生理性唤起(各种形式的睡眠障碍最常见,也表现为作业困难,易激怒及紧张;灾难性事件的滞后或延长反应导致稳态失衡和心身障碍)。常见于残酷的战争、灾难事故、暴力伤害的身受或目击者;表现的症状为反复出现创伤体验,持续的警觉性增高或回避,也可表现为普遍性的反应麻木。[18]
中国的创伤心理治疗师施琪嘉在《创伤心理学》中写道:
心理创伤在既往常指日常生活中的与精神状态相关的负性影响,常由于躯体伤害或精神事件所导致,它可以事件的当事人为载体,但也可能因目睹事件而诱发。在分类上大致可以将这些来源区分为危及生命的“天灾”与“人祸”。前者如自然灾害(洪灾、火灾、旱灾、飓风、地震等),后者如空难、交通事故或战争等。暴力侵犯、被监禁、被折磨、持久被虐待的经历也常常遗留心理创伤。[19]
以上由当代中外医学界、精神病学界提出的权威阐释中,对创伤症状的描述大体一致,但存在一个明显的争论点,就是关于一个事件是否满足诊断性定义,是否是“创伤性”的。美国精神病协会在2000年的修订版中将创伤定性为“涉及死亡或死亡威胁,或其他危及身体完整性的事件”,此前,即1980年和1987年的定义中也有这样的表述,即“将对心理完整性的威胁作为有效的创伤形式”[20]。赫尔曼也把创伤局限为威胁人的生命、身体安全的事件。这类说法招致了一些研究者的批评,因为它们将“仅有严重的沮丧但没有受到生命危险的事件——如极严重的情绪虐待、重大的丧失或分离、降级或羞辱、被强迫(但没有受到身体的威胁和迫使)发生的性经历”的创伤性事件给排除掉了,这无疑“会导致一般人群中实际创伤发生的程度被低估,也会降低某些经历了明显的创伤后疾患的个体被诊断为应激性障碍的可能性”[21]。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医学界则将给精神状态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的事件都纳入创伤事件的范畴。本论文也将采用这一宽泛的界定,即认为,在一定时间内耗尽了人的心理能量,使人的心理完整性遭到威胁的事件都是创伤性事件,因为“经历了其主要心理完整性被威胁的人和身体受到伤害或生命受到威胁的人是一样痛苦的”[22]。
受医学界、心理学界的影响和启发,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也对创伤进行了阐释。在《创伤:记忆的探询》中,文学批评家、创伤理论家卡西·克鲁丝(Cathy Caruth)对1980年美国精神病协会正式承认的PTSD进行了评述:
创伤后应激障碍包括了以前被命名为弹震症、战壕压力症、滞后的压力综合症和创伤性神经官能症,以及对人类和自然灾难所产生的反应。一方面,这种分类和对与之相应的病状的正式承认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类诊断。它包括了与之相关的一切:根据创伤后应激障碍,战争和自然灾难,强奸、虐待儿童和其他的许多暴力事件所产生的反应都已经被理解,一些分离性紊乱症状也可以归于创伤。另一方面,这一有效的新工具在提供了一切的同时却未能为此疾病提供一种实质的解释……[23]
基于对广泛意义上PTSD诊断类别的认可,克鲁丝提出了自己对创伤的认识:“创伤的病理只蕴含在它的经验或接受的结构中:事件在发生的当时没有被透彻理解或体验,只是被延迟,反复控制当事人。准确说来,遭受创伤就是被一种印象或一个事件所控制[24]。”在《无言的经历:创伤、叙事和历史》中,克鲁丝对创伤作出了更完整的界定:“在最广泛的定义上,创伤是突发事件或灾难性事件导致的那种压倒性的经历,其中,人们对于这一事件发生时的反应,常常是延迟的,以幻觉和其他侵入方式反复出现,无法控制。”[25]克鲁丝认为创伤事件在它发生之时没有被充分认识,后来不断侵扰当事人并导致强烈的情绪危机才成为“事件”。显然,她对创伤的时间断裂的强调,吸收了弗洛伊德的概念“延迟行为”(deferred action)或“事后影响”(afterwardsness),从而建构了自己的定义。
此外,耶鲁大学的创伤理论家德瑞·劳伯(Dori Laub)教授也提出了对于创伤的看法:“创伤幸存者并不生活在关于往昔的记忆中,而是在不能也没有继续进行到底的事件中生活。事件没有结束或终止,因此,好比幸存者所担心的,它在各方面都持续到当下。实际上,幸存者没有真正触及创伤现实的核心,也没有重演之前的悲剧命运,于是陷于两者之间。”[26]美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 Capra)在《写历史,写创伤》中写道:“创伤是一种经验发生粉碎性断裂或中断的症状,这种经验会发生滞后效应。”[27]
有关创伤的定义众说纷纭,至今没有达成一种完全一致的说法。目前,人们倾向于接受和引用克鲁丝的定义。但上述种种,从弗洛伊德到克鲁丝,实际上都强调了构成创伤的两个核心要素,即事件本身和主体对于事件的反应,不过存在表述上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创伤定义侧重于列举创伤事件的类别,后来,研究者越来越关注主体对于创伤事件的症候性反应,而不是事件本身。这些症候性反应就是创伤事件造成的影响,即“事后性”。综合上述定义,具体说来,“事后性”就是创伤事件发生一段时间后,当时的情形会以记忆、“闪回”(flashback)、“侵入的幻觉”(intrusive hallusinations)、“噩梦”(nightmare)等形式反复骚扰受创主体,使其不得安宁,形成精神创伤,表现为“极度沮丧”(extreme distress)、“被击垮”(overwelmed)、“强烈的恐惧”(intense fear)、“彻底的无助感”(complete helplessness)等。因此,创伤是主体遭受的创伤事件,更主要的是蒙受事后影响而导致的极端不良的心灵状态或精神状态。创伤的特质在于,它基于真实而残酷的事实,更存在于对该事实的反复体味中,但由于主体不可能真正回到该事件中,因此,它也基于不完全真实的事实体验,形成一种存在的悖论。
创伤还具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事件与主体对于事件的反应,作为形成创伤的两个要件,一是客观性的,一是主观性的。一个事件是否为创伤性事件,是否会形成心理创伤,除了它本身的性质,还取决于主体对客观事件的体验。弗洛伊德说:“症状具有意义,它与病人的体验有关。”[28]面对同一个事件,有人一触即溃,有人却安然无恙。对前者来说,这个事件就是创伤事件,它导致了心理创伤;对后者来说,这一事件不是创伤性事件,没有形成心理创伤。这种迥然不同的结果,与个体的心理因素等相关。心理素质差的人相对心理素质良好的人,易于产生创伤体验,形成创伤经历。虽然诸多创伤定义没有对此进行比较、分析,但不难发现,学者们常用这些词语来描述受创主体的心理素质:“无力应对”(inability to cope)、“脆弱不堪”(vulnerability)、“无法抗拒”(overwelming)、“无能为力”(powerless)等;还对他们的心理机制进行了剖析,克鲁丝说:“创伤就是遭遇某一无法预料或极其恐怖的事件,先前的知识没能为它做好准备。”[29]此外,个体不同的生活经历、文化程度,甚至所处的不同文化环境等因素也会影响创伤体验的形成与否。例如小手术这种事件,对一位缺乏人生经验的儿童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但对屡受挫折的成人也许算不上一回事儿。因此,创伤带有相当的私人维度。如乔恩·艾伦(Jon Allen)所说,“正是对客观事件的主观体验,构成了创伤。……你越相信你身处险境,你的创伤就越严重”。[30]也如卡鲁丝所说:“在简朴的创伤定义中隐藏着一个特别的事实:创伤的病理无法定位于事件本身,事件也许是、也许不是灾难性的,也许并非对每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创伤性……在某种程度上,创伤的病理仅仅在于创伤经验的结构或接受中……”[31]
可见,当代学者在借鉴弗洛伊德有关精神创伤看法的基础上,强调了构成创伤的两个基本要素,同时,也对弗氏定义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一方面,不再将精神创伤现象局限于人类童年甚至更早时期的经验,而将其扩展到威胁人的心理完整性的一切经历;另一方面,不再认为心理创伤只是个体被动地接受某种经验从而给大脑造成强有力刺激的结果,而认为精神创伤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是“由创伤情境作用于主体,经由主体条件的过滤、选择而成的反应”[32]。
鉴于以上的分析、理解,我们认为,精神创伤是创伤事件作用于主体,使主体蒙受事后影响而导致的极端不良的心灵状态或精神状态;它是经由主体条件的过滤、选择而成的一种主观体验的结果,具有个人性特征。
应该注意的是,当创伤事件关涉一个整体,如国家、民族和集体的时候,受创主体就要推及群体,从而有了“集体创伤”“种族创伤”“文化创伤”等概念。因而,创伤的定义虽然基于个体的人提出,但并不影响我们对群体创伤的理解,因为不管受创主体是个体还是群体,首先必定是单一的个体。
(二)创伤与复原
在明确了创伤定义的基础上,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的是,作为体现精神创伤的创伤后症状,是受创主体为应对创伤经历而发展的一种适应性和康复性症状,即心灵自身具有适应创伤事件并且从中复原(recovery)的能力,虽不一定总能成功;此外,导致精神创伤的事件给人带来不幸的同时,也能促进人的精神成长甚至超越。长期以来,受弗洛伊德影响,研究者局限于将精神创伤当作一种消极的、病理性的现象进行探讨,而忽略了心灵对创伤事件所作出的这种积极反应和创伤产生的正性效应。
众所周知,面临外在事件和环境,人类心灵具有内在的自我调节、适应和更新的机制和功能。心理学家将这种内在的适应机制和自我调节过程表述为“自发性”(spontaneity),它通常“会在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之间斡旋,并且负责一个人的情绪平衡”[33]。每一个个体在遭遇创伤事件后,都会动员自己的全部能量,去适应创伤情境,调整心理结构。对创伤性事件的侵入性的再体验是受创者心灵的一种自然自发形式。大脑中以闪回、噩梦或其他形式重现的创伤经历都源于人们对促进创伤事件的现实适应能力、系统地对情绪进行消除所作出的尝试。“这些复活的体验的内在功能是去处理和整合令人沮丧的材料。这说明出现与创伤相关的症状,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们试图去‘代谢’或者内在地解决痛苦的思维、感受和记忆的努力”,在此意义上,那些重现或复活的创伤后应激症状可以被看作是人类心灵应对创伤经历的“一种适应性和康复性症状而非内在的病理性症状”[34]。这种机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受害者在没有进行任何治疗的前提下,几个月就能从创伤情境中恢复过来。事实上,很多早期的创伤后症候反应,其实就代表了个体正在进行自我治愈的努力。治疗师格林(Green)发现,一般来说,经历创伤事件后,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发展出全面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症状,而其中的半数哪怕没有接受治疗,其症状也会在一段时间后消退。
然而,有些创伤经历是如此令人痛苦,它们所激发的负面情绪远远超出了受害者的承受能力,以至于不能被轻易击退,只会让人们反复体验却无法经历一个“正常”的创伤恢复过程,最终使人失去心理平衡,陷于混乱和绝望状态中,出现各种精神症状,甚至导致精神崩溃。Moreno将此状态称为“失去自发性”(loss of spontane ity)。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就必须接受心理治疗。有学者曾说:“创伤经验是被囚禁的人生旋律,它们必须被演奏,必须在人类生命的乐团中被表现出来,而且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世界的乐团中演奏属于自己的音乐(1980)。”[35]如果创伤经验是“被囚禁的人生旋律”,那么必须“被演奏”“被表现”就是创伤的治疗。
由于创伤具有个人化特征,创伤的症状复杂多样,治疗方法也有许多种,如暴露疗法、认知疗法、内隐感受疗法等。但不管采取哪种方法,创伤治疗都应该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进行。因为,创伤与人际关系存在双向联系:创伤影响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反过来能够冲击创伤。首先,创伤常常发生在人与人的交往当中,受创者对他人失去信任,会导致自我与他人的疏离,如赫尔曼所认为的那样,“幸存者对基本的人际关系的质疑……打破了家庭、友谊、爱以及对共同体的依赖……打碎了在与他人关系中形成和保持的自我建构”[36]。其次,对于一个已经有了创伤经历的人来说,其人际关系极有可能受到影响。因为受害者通常会感觉无能为力、无助、不能自主,丧失自我感觉能力、独立能力等,包括形成健康的人际交往能力。用 Lindemann的话来说,就是“创伤可以定义为一种亲密联结的破坏”[37]。最后,遭遇创伤后,最先要恢复的是基本能力,这些能力在与人相处中形成,也要在人际交往中恢复。如果当事人能获得更多的人际关系或支持,那么也能更快地从创伤中恢复过来。由于创伤与人际关系的这种复杂联系,帮助受害者改进和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了解那些有风险的人际关系,对于其从创伤中复原、找到创伤后的新生活变得十分重要。所以,创伤不能独自面对,只有“在关系中”才有康复的可能。中国学者李桂荣也认为:“心理创伤的核心问题是患者能力的丧失和与他人的疏离。所以,创伤治疗的根本途径是患者能力的恢复和新的人际关系的建立。”[38]此外,社会文化环境也有助于受创者走出创伤,“在个体如何应对潜在的创伤经验方面,文化起着关键作用。文化提供了背景。在这一背景中,可以体验到社会援助和其他积极的、振奋的事件”。[39]赫尔曼、拉厄(Rahe)、拉撒路(Lazarus)等理论家,在创伤、个体和文化的关系上做了许多的研究工作。他们认为,个体与其所生活的环境或社区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重要,这种互动决定着个体能否应对潜在的创伤经验。
恢复与外界的联系、重建人际关系是创伤复原的根本途径,而创伤叙述又是这一途径中的关键环节,因为叙述是人与人交流的主要方式。创伤叙述包括口头讲述和书面表达,书面表达又有证词、电影、历史、文学等表现形式。受创者通过讲述或写作创伤经历,将零散的创伤记忆整合成创伤事件,能够释放情绪,缓解症状。早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贾内和弗洛伊德对歇斯底里症做完各自的研究后,就得出了这个非常惊人的相似的结论:当创伤记忆及其引发的剧烈情绪被复原,且通过言语表达时,歇斯底里的症状就会减缓。在《关于歇斯底里的研究》(1895)中,弗洛伊德也主张:“当病人最大可能详细地描述事件,将情感放入词语中时,每一个个体的歇斯底里症状都会立即而永久地消失……”[40]弗洛伊德把这一过程称为“宣泄”(catharsis)或“净化”(abreaction),并且发展出“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这种方法成为现代精神治疗的基础。普林斯顿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斯宾塞·唐纳德(Spencer Donald)把弗洛伊德称为“叙事传统”的“大师”,因为他善于将当事人“支离破碎的联想、梦和回忆的片段”编织成连贯完整的故事,“让我们认识到连贯的叙事的说服力量……似乎毫无疑问,一个建构得很好的故事包含一种叙事真理,它是真实地、直接的,对于治疗性的转变有重要意义”。[41]贾内把对创伤的叙述称为“叙述记忆”,对“叙述记忆”和“创伤记忆”作出了区分,认为创伤记忆是对历史的重演,精确而又僵硬,叙述记忆却能够临时制作历史,正是二者的转换表现了从创伤中康复的过程。拉卡普拉回应了弗洛伊德和贾内的主张,提出“通过”(working-through)概念来描述文学文本在表现创伤时的作用,认为写作“必须暗示着与创伤的距离,必须内在的是一种治疗过程”[42],从而重申了对叙述作为治疗的强调。在现代心理治疗中,已经有了专门的叙事治疗(narrative therapy)法。叙事治疗就是当事人通过叙说,把事件“外化”,即把人与事件分开,不把它当成自己的一部分,通过把它放在一个故事情境中,当成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当事人就可以从抑郁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如台湾研究者周志建所论述的那样:“叙事治疗透过所谓的‘外化’,将人与问题分开,问题不等于人,问题的本身才是问题(吴熙瑄,民90)。这样外化的观念源自迈克尔·怀特(Michael White)(1991),他将问题视为一个分离、存在于个人之外的实体,以将它客观化的方式,让人可以跳出原来‘人等于问题’的框架,重新看待问题的本质,让人可以有新的选择,避免被问题所压迫。”[43]大陆学者也说,“无论如何,叙事都是个人精神创痛得以救治和疗效的必经途径”。[44]
其实,创伤叙述不仅仅是需要接受治疗的受创者的必由之路,对于那些通过自我心理调节而复原的受创者,也能够将他们已经做出的康复努力最优化。具体体现在,受创者通过叙说,还能够对创伤事件产生新的体验,对人生形成新的、积极的认识。如周志建所总结的那样:“透过叙说,叙事者在不断地叙说自己生命历程中,会将过去零散的记忆与经验做一个统整,藉此理解自我的生命意义,并重新对自我生命得到新的体验与领悟,进而发展自己生命意义的图像……。”[45]
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认识到的是,通常,从创伤中走出,受害人对自我的认识会有所增加,对人生、生命的看法会更为深广,从而实现精神的飞升。换句话说,创伤性经历除了引发人们的痛苦情绪外,也能促进成长。“我们发现不幸和痛苦——除了会导致混乱和伤害之外——时常也会推动人们发展出更积极方式。……这可能包括新的心理复原的水平、更多的生存技能、更好的自我了解和自我欣赏、共情能力增加、对生命的看法更广泛和全面……”[46]例如,经历过自然灾害和重大疾病的人,会倍加珍惜生命。失去亲人尤其是丧失配偶的人,会变得更加独立和坚强。诚如巴尔扎克所说,创伤体验“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
(三)写作治疗及其心理机制
写作是创伤叙述的重要形式之一,具有治疗作用。作者通过语言文字这一载体,将自己的创伤经验诉诸笔端,能够舒缓或消除精神紧张、心理压力,释放负面情绪,促进身心健康。写作式样很多,有日记、书信、博客、传记和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而且,写作有着口头表达所不具备的便利性和安全性。创伤性经历都由负面、痛苦的事件构成,引发出的是消极的情绪体验。所以,当事人的感受和看法更具有私密性,不便于公开谈论或讲述。书面表达则是一个相对的安全地带。例如,日记作为一种最普及的写作方式,它的读者仅仅是作者本人,作者可以将自己不愿公开的情感体验尽情地、毫无顾忌地、畅快淋漓地倾诉出来,达到彻底的“宣泄”。博客是网络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型日记,或称网络日志,相比传统日记,有一定的公开性,又有一定的私密性,它既是一种社交工具,也是人们表达情感的天地。日志者可以有选择性地释放创伤,并且在与人的交流中得到进一步疏通、缓解。在诗歌、小说等写作中,作者也可以自由地控制情感的表露程度,根据自己的意愿,或直接抒发,或通过象征、隐喻等艺术形式隐晦地表达。
目前,在心理学界,关于心理创伤治疗的理论派别有很多,主要的有精神分析理论、认知加工理论、情感压抑理论、暴露与情绪加工理论等。这些理论派别,从各自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写作活动是如何在个体的心灵层面产生治疗效应的。
情感压抑理论认为,写作通过把受压抑的情感释放出来,发生治疗效应。这一观点源于精神分析鼻祖弗洛伊德对宣泄效果的解释。弗洛伊德晚年论述了本能与文明的关系,这一研究成果中蕴含着写作治疗的思想。他指出,“在艺术活动中,精神分析学一再把行为看作是想要缓解不满足的愿望——这首先体现在创造性艺术家本人身上”,“艺术家的第一个目标是使自己自由,并且靠着把他的作品传达给其他一些有着同样被压抑的愿望的人们,使这些人得到同样的发泄”[47]。那么,作为艺术活动之一的文学创作,其治疗效能就体现为将作者现实中未满足的、被压抑的愿望释放出来,同时在虚构的世界中获得补偿。当然,弗洛伊德也论及了文学的读者治疗功能。后来的许多医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认同他的观点,并且作出了补充,认为被压抑的心理负荷得不到释放,长期积于心中,会带来不良后果,如果把它们发泄出来,可以减少压抑造成的紧张,调节身体与心理的平衡,改善多项健康指标。
在认知加工理论看来,创伤写作通过整合创伤事件,可以减少或消除由创伤带来的无意记忆,同时赋予事件以新的意义,从而消除创伤症状,帮助个体恢复。认知加工理论的代表人物 Janoff-Bulman(1992)认为,一切个体都持有三个核心假设:我们是不会受到伤害的;世界是有意义和可以理解的;我们都从积极的角度看我们自己。[48]然而,由于创伤体验与这些假设的心理图式完全不相匹配,所以一旦发生创伤事件,原有的假设就被统统打破,转而认为世界没有意义,人生没有安全感,也对自我产生怀疑。这时,受创个体就要改变已有的心理图式去适应创伤体验,或者把创伤体验整合为连贯的叙事,与原有图式相匹配。在创伤写作中,一方面,受创者可以把零散的创伤记忆整合为系统、连贯的叙事,从而消除创伤带来的负面情绪,减少对创伤事件的再体验。“这个整合过程通过减少负面情感的唤醒,最终导致身心症状的减少[49]。”另一方面,受创者将曾经经历的富于积极意义的生活片段整合到创伤叙述中,构造出与创伤记忆中的事件具有相反意义而与原有心理图式相吻合的新故事,无疑有助于自我复原。
依据暴露与情绪加工理论,受创者遭遇创伤后,常常会力图逃避生活中那些与创伤事件相关的刺激。这种逃避行为,阻碍着他们去适应创伤经历,也阻碍着他们对创伤事件的重新认识以及采取新的应对措施,因为创伤性情境得不到再现和加工。PTSD的相关症状就是由这种逃避引发的。有研究者将 PTSD 的暴露疗法分为两步:“首先是对创伤有关的最痛苦的记忆、画面和情绪反复地自我面质,从而通过对他们达到适应而减少PTSD症状。这个过程可以通过想象暴露或实体暴露来实现。接着是让个体挑战对创伤不合理的认知和想法,对创伤事件做出崭新的诠释和理解,并评价他们的应对策略。”[50]据此观点,多次创伤性写作使受创者反复暴露于创伤情境中,不断接受也不断适应相关刺激,并且在想象和虚构的世界中放弃对于创伤的不合理认知和想法,形成新的理解和积极的认识,逐渐排除创伤事件留下的阴影。
上述理论都对创伤写作的影响机制作出了解释。这些解释各有侧重,也有交叉,且互为补充,说明心理学界对写作的心理治疗功能有了全面、充分的认识。综合起来,就是写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通过回忆创伤经历,激活与创伤有关的各种负面情绪,重构和加工创伤事件,把它整合为连贯的叙事,与原有认知图式相匹配,使个体受压抑的潜意识欲望得到宣泄,或者使个体完成对创伤刺激的适应,减少对创伤经历的再体验,从而消除创伤症状,调节身心平衡,并且激发心灵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和生命活力,使作者在生活中无法实现的、被压抑的愿望在想象的世界中获得补偿。
20世纪末,随着文学治疗的理念被译介到国内,中国学者对写作治疗及其发生原理也有着自己的理论阐述。叶舒宪先生提出,文学活动能满足人的高级需要。它们是:符号(语言)游戏的需要、幻想补偿的需要、排解释放压抑和紧张的需要、自我确证的需要和自我陶醉的需要。[51]并且认为,每个个体都有这些需要,不过不同的个体会有各自不同的侧重;这五个方面相互作用、彼此交织;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需要不能满足,整个精神生态系统就会失衡,导致精神疾病。正是这些内在需要为写作治疗“提供了精神生态上的依据”[52]。因为文学创作作为一种叙事活动,便于创作者倾诉自己的心绪和体验;作为一种审美想象活动,能够充分调动创作者的想象和幻想能力,在虚构的文学世界中憧憬未来,重建自我,确立新的人生目标,找到自信和自我价值。个体由于遭遇创伤事件而产生的某些需要可以在写作中获得满足,使受损的精神生态系统得到修复,回归正常状态。
中外学者的种种研究和论述表明,写作可以疗伤。事实上,目前,写作治疗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心理医学领域,成为心理医生对病人进行治疗的重要方法,也成了作家们发泄情绪,以达到养生目的的一种手段。
翻开古今中外文学史,不难发现,无数作家由于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原因,心中充塞着积怨、痛楚或悲愤,于是诉诸笔端,以求一吐为快。比如,村上春树说:“我认为,写小说更多的是自我治疗的行为。有人也许会说,由于有了某一信息才将其写成小说,但至少我不那么认为。我倒感到:是为了找出在自己心中有怎样的信息才去写小说的”[53],写小说的过程“对我来说,是最终的游戏,是自我治愈”[54]。中国当代作家史铁生在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写作时,也回答说:“去除种种表面上的原因看,写作就是要为生存找一个到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这道理真简单,简单到容易被忘记。”[55]
许多作家的创作经历表明,写作的治疗作用是客观地存在着的。但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写作治疗并非在所有作家身上都会产生同等效应。万事万物都有两面性,文学也不例外。罗兰·巴特曾说,词语既可以充当药物,又可以成为毒物[56]。写作到底是发挥“药”的功效,还是产生“毒”的副作用,在于作家本人的自我把握。如但丁、狄更斯和鲁迅等,利用想象和虚构的文字世界重新构筑出自己的人生故事,并对它们产生新的认识和理解,一方面及时释放了创伤情怀,另一方面改变了对于生活和自我的看法,建构起一个新的、积极的自我,从而成功地保护了自己。而川端康成,由于没能处理好“幻游治疗”与“走火入魔”之间的矛盾,敌不过“药与毒之间的张力”[57],最终选择了自杀。这类作家也不在少数,还有海明威、普拉斯、三毛等。所以,我们在谈论写作的治疗功效时,要因人而异,不可随意夸大。此外,作家的治疗性写作,有出于自我抚慰的动机,有时也不外乎社会的需要,例如鲁迅。其实,不管作家的创作动机如何,其作品客观上都会对读者产生治疗作用。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调动自己的审美想象能力,与作品世界接轨,并产生认同,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建构,由此实现心灵的净化与情感的升华。
二 研究价值
心理创伤学视角的选择,当代心理创伤理论与方法的应用,为研究伍尔夫文学提供了一种更为全面、深入的解读方式,为伍尔夫研究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这种研究具有极大的价值。
第一,进行伍尔夫精神创伤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主要体现为两方面。
首先,本选题基于伍尔夫的生平与创作,伍尔夫研究现状,以及笔者长期以来对伍尔夫的阅读与思考,提出运用心理创伤学理论对伍尔夫及其作品进行审视和研究。这种研究将伍尔夫的生平经历、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以及她的政治意识与文化思想进行综合考察,有助于伍尔夫研究的更加全面化、系统化,也有助于将伍尔夫心理分析研究推向纵深层面,是对伍尔夫研究的极具意义的补充。
其次,本选题也针对当前文学中的创伤研究状况提出。关于创伤问题的研究可谓由来已久。对创伤的系统性研究则始于19世纪末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派成员,他们发表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对其他许多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创伤往往由外部事件引发,外部事件使人遭受创伤后,创伤会内化于人的心灵世界,变成人的一种内在体验,于是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应对创伤。这种思考始于创伤,围绕创伤,其结论也涉及创伤。这样,创伤成为我们思考暴力、体验伤痛和反思文化伦理的有力工具。自进入频遭创痛的现代社会以来,几乎所有的文化史都会论及创伤。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自然也在书写着创伤、思考着创伤。今天,现代性语境下的创伤问题研究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领域已成系统,硕果累累。而从创伤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是国际文学界进入21世纪以来才出现于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新动向,显得十分零散、缺乏系统性,在国内文学批评中则更为少见。在文学领域系统地研究创伤问题显得十分迫切。因此,本选题也有利于深化文学中的创伤研究,尤其是有助于促进国内创伤文学研究。
第二,进行伍尔夫精神创伤研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主要体现为三点。
首先,在现当代英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化这一大的背景之中,在心理创伤理论的视域下,对伍尔夫及其作品展开全面、系统的分析考察,指出伍尔夫创伤经历与文学创作的紧密关联,认为其作品是对英国现代社会问题以及西方创伤文化最为全面、最为丰富,也是最为复杂地揭示和表现,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伍尔夫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本质特征,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伍尔夫在西方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影响。
其次,也对伍尔夫创伤体验的由来、释放、治疗和超越进行了细致的描述、阐析和评判,这种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众所周知,创伤是人类生活无法回避的一部分。人类历史是文化艺术的历史,也是应对暴力、战争和自然灾难的历史。人类从苦难中走过了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和此起彼伏的种族冲突。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依然面临着各种天灾人祸。在中国,先后经历了洛阳12·25特大火灾(2000—2001)、大连5·7空难(2002)、非典型性肺炎(2003)、汶川大地震(2008)、幼儿园事件(2010)、校车事件(2011)等。逝者已远行,生者乃长痛。如何有效地抚慰伤者,治疗创伤?除了千百年来人们积累的非科学的、迷信的仪式,以及医学的治疗方法,文学疗伤也日益成为题中之义。因而,探讨伍尔夫如何通过文学活动实现治疗伤痛并且超越自我的目的,无疑对处于生存困境中的当代人的人生具有借鉴和教育意义,尤其对于遭受重大创伤事件后的人们的心理朝正性发展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从而也体现出学术与现实相结合和学术为现实服务的品格。
最后,本研究还对伍尔夫的创伤写作作出了价值判断,认为她的作品准确传达了个体创伤经验,并且将个体经验上升为普遍的人类经验,表达了对于生命的热爱和关注,确立了生命的维度。与之对照的是,新中国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之后,虽然中国文坛涌现出了以热烈讨论文革创伤、全面反思政治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创作浪潮;但中国的“伤痕”和“反思”文学中的创伤讲述为呈现“政治创伤”而刻意遮蔽了对个体创伤体验的表达,为国家意识形态所规训和征用,这种为特定意识形态而建构的叙事由于偏离了个体创伤记忆而缺乏生命的维度,不能有效地抚慰创伤,也有悖于创伤的生命本质。因此,本研究对于反省我们已有的创伤书写,以及对于我们今后的创伤性表达写作均具有启发性和借鉴作用。
[1][英]弗吉尼亚·伍尔芙:《班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载[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Ⅱ),王义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01页。
[2][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页。
[3]瞿世镜:《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理论》,载[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页。
[4][英]伦纳德·伍尔夫选编:《一位作家的日记》,转引自瞿世镜《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34页。
[5]陆扬、李定清:《伍尔夫是怎样读书写作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6]陆扬、李定清:《伍尔夫是怎样读书写作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7]陆扬、李定清:《伍尔夫是怎样读书写作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8]陆扬、李定清:《伍尔夫是怎样读书写作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9]Pierre Janet,L'Automatisme Psychologique,转引自卫岭《奥尼尔的创伤记忆与悲剧创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10]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4卷,长春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页。
[11]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4卷,长春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页。
[12]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4卷,长春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页。
[13]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Diagnostic and Statisti cal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ourth Edition[DSM-Ⅳ],Washington,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1994,p.428.
[14]参见[美]约翰·布莱伊尔等《心理创伤的治疗指南》,徐凯文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15]参见施琪嘉《创伤心理学》,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2页。
[16]参见施琪嘉《创伤心理学》,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17]Judith Herman,Trauma and Recovery,London: Pandora,2001,p.33.
[18]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会、南京大学脑科医院:《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7—88页。
[19]施琪嘉:《创伤心理学》,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20]参见[美]约翰·布莱伊尔等《心理创伤的治疗指南》,徐凯文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21]参见[美]约翰·布莱伊尔等《心理创伤的治疗指南》,徐凯文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22]参见[美]约翰·布莱伊尔等《心理创伤的治疗指南》,徐凯文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23]Cathy Caruth ed.,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3.
[24]Cathy Caruth ed.,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p.4-5.
[25]Cathy Caruth,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11.
[26]Dori Laub,“Bearing Witness or the Vicissitudes of Listening”,In Shoshana Felman and Dori Laub,ed.,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Psychoanalysis,and History,New York and London: Rutlede,1992,p.69.
[27]Dominick La Capra,Writing History,Writing Trauma,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p.186.
[28]Sigmund Freud,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New York: Boni and a liverinight,1920,p.221.
[29]Cathy Caruth,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153.
[30]Jon Allen,Coping with Trauma: A Guide to Self-understanding,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1999,p.14.
[31]Cathy Caruth,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4.
[32]唐晓敏:《精神创伤与艺术创作》,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33][瑞典]彼得·费列克斯·凯勒曼、[美]M.K.赫金斯:《心理剧与创伤——伤痛的行动演出》,陈信昭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34][美]约翰·布莱伊尔等:《心理创伤的治疗指南》,徐凯文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
[35][瑞典]彼得·费列克斯·凯勒曼、[美]M.K.赫金斯:《心理剧与创伤——伤痛的行动演出》,陈信昭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36][美]朱迪斯·赫尔曼:《创伤与复原》,杨大和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5页。
[37][瑞典]彼得·费列克斯·凯勒曼、[美]M.K.赫金斯:《心理剧与创伤——伤痛的行动演出》,陈信昭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38]李桂荣:《创伤叙事:安东尼·伯吉斯创伤文学作品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
[39]Marten W.De Vries,Trauma in Cultural Perspective,N.Y.: The Guilford Press,1996,p.3.
[40]Sigmund Freud and Joseph Breuer,Studies on Hysteria,London and New York: Penguin,1991,p.57.
[41]Spencer Donald,Narrative Truth as Histori cal Truth,New York: Norton,1982,p.21.
[42][英]安妮·怀特海德:《创伤小说》,李敏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页。
[43]周志建:《叙事治疗的理解与实践》,硕士学位论文,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2002年,第3页。
[44]李明、杨广学:《叙事心理治疗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121页。
[45]周志建:《叙事治疗的理解与实践》,硕士学位论文,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2002年,第3页。
[46][美]约翰·布莱伊尔等:《心理创伤的治疗指南》,徐凯文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47][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美学上的应用》,载[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陈伟奇译,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
[48]张信勇:《写作疗伤--表达性写作对创伤后应激反应的影响及其机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第15页。
[49]张信勇:《写作疗伤--表达性写作对创伤后应激反应的影响及其机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第72页。
[50]张信勇:《写作疗伤——表达性写作对创伤后应激反应的影响及其机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第86页。
[51]叶舒宪:《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文艺研究》1998年第6期。
[52]叶舒宪:《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文艺研究》1998年第6期。
[53][日]河合隼雄、村上春树:《村上春树拜谒河合隼雄》,(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66—67页。
[54][日]河合隼雄、村上春树:《村上春树拜谒河合隼雄》,(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69页。
[55]史铁生:《史铁生作品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页。
[56][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268页。
[57]叶舒宪:《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文艺研究》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