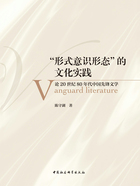
第三节 研究现状评析
80年代先锋文学的研究几乎与先锋文学创作是共时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80年代先锋文学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本来就是不断将其“经典化”的过程。在80年代特殊的历史时空中,文学场的生成过程就是对于文化权力的争夺过程。先锋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42],具有“自律文本”与“社会事实”的双重性,因此,它与所有现代艺术进入文化场域时的情形一样,是话语权力抗争与妥协的结果。[43]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锋文学研究在80年代即已开始。而且许多批评家与先锋作家私交甚笃,对于先锋文学既有观察者的客观冷静,也有参与者的情绪冲动。
以先锋文学现象或思潮作为研究对象的论著,笔者目前查阅到的主要有:《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现代性》(陈晓明著),《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张清华著),《守望先锋——兼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发展》(洪治纲著),《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吴义勤著),《先锋试验: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先锋文化》(尹国均著),《新时期先锋文学本体论》(焦明甲著),《先锋的姿态与隐在的症候——多维理论视野中的当代先锋小说》(刘云生著),《中国先锋诗歌批评研究》(崔修建著),《中国后现代——先锋小说中的精神创伤与反讽》(杨小滨著),《20世纪中国先锋诗潮》(罗振亚著),《欧美先锋文学与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王永兵著),《先锋的魅惑》(张立群著),《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叶立文著),《先锋及其语境——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研究》(程波著),《叙述的狂欢与审美的变异:叙事学与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南志刚著),《先锋小说的兴起》(李建周著),《审美的悖反:先锋文艺新论》(王洪岳著)等。综合研析现有文献和成果,目前学界对于先锋文学的研究主要呈现以下两种类型。
一 80年代先锋文学的思潮研究
后“文革”时代开始后的十年是中国人文思想领域极大活跃的十年。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80年代是一个绕不开的参照系。文学社会学的法则对于80年代文学研究来说,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和路径。也因此,把先锋文学纳入80年代的文化思潮来考察,是一个最常见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产生的研究成果,在先锋文学研究中是最为出彩的。以研究先锋文学而成名的几位批评家,如陈晓明、张清华、洪治纲等,都是将先锋文学视为一种人文思潮的。
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在先锋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这部论著1993年首次出版,而其写作开始在80年代末,这几乎是一部对先锋文学进行同步观察的著作。陈晓明和余华、格非等先锋作家有着良好的日常生活沟通,因此,他不仅仅是一个文本意义上的批评家,同时也是对先锋作家生活有着情感介入的参与者。《无边的挑战》多次再版,也证明了这种熔作家观察与文本研究为一炉的治学路子是有重要价值的。
张清华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也是一部具有相当影响的先锋文学研究力作。这部初版于1997年的论著,理所当然地成为研究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必备参考书。张清华这部著作受到了陈晓明《无边的挑战》的一定影响,但张清华扩展了先锋文学的历史纵深,以启蒙主义、存在主义为精神基因来观察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先锋思潮,历史语境、叙事策略和文化逻辑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张清华这本论著的显著特色。《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既有逻辑论证,又有文本分析,同时亦颇有创见的文本价值判断,甚具相当的历史厚度和理论创新。
2000年开始,洪治纲在《小说评论》开辟了“先锋聚焦”专栏,发表了系列研究文章18篇,约20万字,在先锋文学研究同行中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先锋文学出现二十年后的2005年,洪治纲的博士学位论文《反叛与超越——论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通过答辩。当年,即以《守望先锋——兼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发展》为书名出版。洪治纲的论著同样是着眼于先锋文学思潮的。因此,历史境遇、主体向度、艺术实践、文本动向成为洪治纲考察先锋文学的重点。
除了前述三位学者,着眼于先锋文学思潮和现象研究的重要著作还有:叶立文的《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刘云生的《先锋的姿态和隐在的症候——多维视野中的当代先锋小说》,尹国均的《先锋试验: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先锋文化》,焦明甲的《新时期先锋文学本体论》,王永兵的《欧美先锋文学与中国当代先锋小说》,李建周的《先锋小说的兴起》,杨小滨的《中国后现代——先锋小说中的精神创伤与反讽》等。此外,张旭东的《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作为精神史的80年代》,程光炜主编的“重返80年代”丛书(《重返80年代》《文学讲稿:“80年代”作为方法》《文学史的潜力——人大课堂与八十年代文学》等),以及李杨、洪子诚、程光炜、王尧、张旭东、贺桂梅、杨庆祥、黄平、李建周等学者的“重返80年代”的相关论文论著中,亦有对于80年代先锋文学思潮颇有学术价值的反思。程波的《先锋及其语境: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研究》,郝魁锋的《先锋之后的文学踪迹——20世纪90年代后“先锋小说”转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对80年代先锋文学的兴起与90年代先锋话语的渐变进行了结合文本的探究。
思潮研究注重的是先锋文学产生的特定语境,并把它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现象来予以审读。由于西方理论在研究材料中的注入,对于先锋文学思潮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其学理性很强,体现了学者们对于80年代先锋文学的理性思考。
二 80年代先锋文学的文本研究
先锋文学之所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脱颖而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文本的独具一格,先锋文学掀起的文学革命就是一场形式的革命。把作家作品作为文学批评的样本,是先锋文学研究最为基础的工作,对于先锋文学的命名,就是在此基础上实现的。
80年代中后期,上海的批评家群体[44]对先锋文学迅速扩大影响产生了很大作用。吴亮的《向先锋派致敬》《马原的叙述圈套》等先锋文学批评名篇即是那个特定年代的产物。北京的李陀同样是先锋文学的吹鼓手,他为现代派的辩护至今仍对先锋文学研究具有启示性。在以先锋作家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中,吴义勤199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是重要的论著之一。吴义勤通过自己敏感的文学阅读和扎实的理论素养,对重要的先锋作家以及重要的先锋作品进行了评析,即使现在翻阅这本论著,其评论依然相当精当,且具有一定前瞻性。洪治纲的《余华评传》是以评传方式对先锋作家进行深入研究的论著,该书将余华的人生履历、创作历程、作品呈现结合起来评价,具有史料价值,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王琮的《90年代以来先锋小说创作的转型——以苏童、余华、格非为代表》,对三位先锋作家既有整体风格的把握,亦有具体文本的精细解读,对90年代之后先锋姿态的转变进行了综合评价,对先锋风格流变有很好的基于文本个案的分析;南志刚的《叙述的狂欢与审美的变异——叙事学与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立足于文化本土化和审美主体性两个基点,对马原、余华、莫言、苏童、格非等作家的先锋小说进行了叙事以及审美特征的分析,比较叙事学的视野为该著增色不少;翟红的《论8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语言实验》,聚焦于先锋小说的最基础构件——语言,在文本细读上颇见功力,可视为对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先锋性的“语言实证”;黄韬的《怪诞意识的自觉与实践——论王小波、莫言、残雪、刘震云、余华等作家笔下的怪诞美》,对先锋文学的怪诞风格进行了美学分析,探究了先锋怪诞美的由来和成因,并对作家作品进行了文学史价值的评价。
对于先锋文学代表作家的研究,21世纪以来不断增加,仅以余华、格非、苏童三人为例,在中国知网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分别输入三位作家的名字,2000—2018年,以余华为研究对象的有309 篇,以格非为研究对象的有104篇,以苏童为研究对象的有177篇。其中,蔡志诚的博士学位论文《时间、记忆与想象的变奏——格非小说创作研究》,张学昕的博士学位论文《南方想象的诗学——论苏童的当代唯美写作》,薛美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基于修辞学视角的苏童小说语言研究》,张枫的博士学位论文《新时期现代主义小说的生命意识书写研究——以余华、残雪、格非、苏童为中心》,在先锋作家个案研究上较为突出。
对于80年代先锋文学的研究,目前成果丰硕。但先锋文学研究依然只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头而已。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或文学思潮,已经在20世纪90年代渐趋沉寂,但80年代先锋文学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依然有着潜在影响,80年代先锋文学的“遗产”值得更加深入地追问和开掘。本书将在吸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重点从以下两个方面介入80年代先锋文学研究。
其一,以话语塑形为考察中心,以80年代的人文、历史语境为背景,梳理80年代先锋文学话语的塑形、弥散与消融。
80年代先锋文学最重要的贡献无疑是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全新的文学知识话语。这种全新的知识话语就是一种文学本位的话语。在80年代先锋文学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样式真正是“唯文学”的。中国新文学的出现本来就是革命政治的产物,新文学运动的许多主将同时也是政治活动家。救亡、图存、启蒙、革命,这样的规定性一直伴随着中国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似乎可以作为中国新文学话语建构史上的两个典型样本,前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45],后者主张“为艺术而艺术”[46],但实际上两者在文学话语的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对于文学“外化”功能的强调,文艺被认为是改造社会(当然包括被认为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工具。因此,“从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47] 成为两者最后的历史命运,一点都不奇怪。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新的国家政权建立。由于东西方阵营意识形态的对立,加之革命政治话语的统摄性影响,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文学话语具有支配性的控制。即使是80年代前期,响应政治口号,紧密配合形势,依然是相当一部分作家的“政治自觉”(事实上也是认知惯性支配下的“文学自觉”)。正因如此,先锋文学话语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出现是革命性的,它“具有无可比拟的话语价值”,因为先锋文学“把本世纪几代中国作家一直想完成而又一直未能如愿以偿的对于文学本体的审美还原现实化了”[48]。
基于上述认知,对于先锋文学话语塑形过程的考察将是本书的一个关键着力点。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动下,后“文革”时代开始后的中国社会萌生的“解总体化”的运动,为文学新变提供了可能性。1949年国家新政权建立之后的社会总体化,其根本策略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运动”[49]。因此,后“文革”时代的解总体化运动,在意识形态维度上,其实就是从革命政治的总体化元叙事中逃离。这种逃离带来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边际化”,正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边际化给文学带来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50] 除了国家(政党)意识形态的转向,解总体化必须还得有国民的觉醒作为支撑。正因如此,80年代是一个启蒙话语主导的年代。启蒙的重点就是“人”,作家主体性正是在启蒙语境中复苏的。作家主体性的重拾,为文学的激进探索提供了主体基础。政治、社会、历史等外在价值一直左右着中国当代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始后,文学价值判断却无法提供新的标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尽管在当时引发巨大关注,但同样没有走出文学政治化的既有逻辑。80年代“美学热”的兴起,恰当其时地为文学新变提供了另外的价值判断体系。尤其“美学热”由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审美政治狂热向美学学科自律转向之后,审美主义成为“美学热”的重要成果,审美自律也因此成为文学的重要价值标准。在80年代,现代化是社会主义中国新的总体化,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在现代化期待中成为文学接受的热点。充满了技术主义特征的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自然而然地成为意欲实现“文学现代化”的中国作家的首选参照物。所以,形式实验为主要特征的80年代先锋文学,完全可以视为中国现代性的附属物。在文化本质上,它对改革时代中国人文知识领域来说,是一种基于现代性梦想的形式意义上的“替代性满足”[51]。“形式的选择”同样是“主体的选择”[52],逃离总体化叙事→启蒙话语→美学热→现代性追求→形式实验,这样一条历史线索大体上提示了先锋文学话语的发生学背景,而这也正是本论著重要的考察路径。除了对人文历史语境的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现象和思潮中隐在或显在的先锋性,亦将是先锋话语谱系考察的另外一个关键点。如果说支撑先锋话语塑形的人文、历史语境是抽象的,那么,文学现象和思潮则是具象的,它包孕或彰显了先锋话语的历史源流。本书将聚焦于“地下文学”“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等文学新变与探索,力图从这些文学现象和思潮中,找出被文学史中“先锋文学”概念剪辑过滤掉的“前先锋”“准先锋”“类先锋”的文学因子,通过先锋文学基因的梳理,最大限度地勾勒出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谱系,并将其与80年代特定的人文历史语境对参,揭示先锋文学形式实验的历史渊源和文学成因。
其二,以“形式意识形态”为理论基点,以文本细读为支撑,探讨“形式自律”为特征的先锋文学在80年代语境中的原生属性。
仅仅就文本来看,80年代先锋文学最显著的特征无疑是形式。在80年代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中,“形式”这个在主流文学意识形态中长期受到贬抑的概念获得解放,迸发出巨大的文学能量,震动了80年代的中国文坛。当然,80年代先锋文学的意义绝非仅止于形式。在意识形态丛林中诞生的先锋文学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53],其“意味”的核心就是“形式意识形态”。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的形式革命,表面上看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逃离,即从政治意识形态的“他律”转向文学形式本身的“自律”,但触发这种革命性转型的原动力依然来自意识形态。伊格尔顿曾言:“文学形式的重大发展产生于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54] 8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国家意识形态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型,革命政治慢慢消融于经济政治和文化政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新变成为80年代的独特文化景观。文学形式发生重大变化,当然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松动,这是主流意识形态默许的结果,但我们同时也应注意到,文学形式本身就包含着它内生的意识形态,在形式这个“掩体”之下,它对主流意识形态事实上形成了政治抗辩。形式化的文本与意识形态其实不可能完全割裂,阿多诺即指出,形式自律的艺术实际上是“凭借其存在本身对社会展开批判”[55]。
本书将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形式意识形态”理论,通过具体的先锋文学文本细读,重点考察80年代先锋文学的语言风格、叙事伦理和精神意象,并对形式实验的文化遗产进行重审,在理论视野和具体文本的对照中,探秘先锋文学形式实验与80年代意识形态的“转换关系”,重现“文本得以产生的通常被取消的意识形态的轮廓”,[56] 以期为80年代先锋文学研究提供具有一定新意的阐释视角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