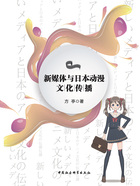
第二节 漫画的时间线索与类型划分
二战后,日本现代漫画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日本动漫开始形成。如果从历史时间的维度分期,可以借用手塚治虫的六大时期论:玩具、追讨、点心、主食、空气、符号。1945年之后的十年间,漫画依然被认为是为儿童设计的肤浅无聊的文化产品,被称为“玩具时期”;随后的十年,由于日本战后民众的精神世界需要廉价的文化产品来填补,所以一些粗制滥造、恶俗阴暗的漫画产品大行其道,漫画遭受很多家长的反对,因此成为“追讨时期”;60年代之后,以少年为对象的期刊慢慢出现,一些开明的家长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允许子女偶尔看漫画书,故为“点心时代”;60年代中期,《铁臂阿童木》的出现,使电视动画成为全家可以观看的广受好评的节目类型,是为“主食时期”;70年代以后,正如手塚治虫所言:“在这个时代,漫画犹如空气”,漫画成为打发闲暇时光、居家旅行、乘坐交通工具时的必备文化产品,这就是“空气时期”的由来;最终,1985年日本动漫黄金时代的到来,使日本动漫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流行文化产品,并进阶为日本形象的代言人,成为全世界漫迷所共有的文化符号,也即“符号时期”。由此可见,日本动漫从雕虫小技变为日本国民喜爱的文化产品,并进而成为全世界范围的流行符号,足以印证文化产品在物质属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创造精神世界,以独特符号建构的精神世界才是文化得以广泛流传的根基。
日本漫画之所以风靡全球,正是因为其内容元素异常丰富,比如美少女、美男子、战争、校园恋爱、喜剧元素、魔法穿越、魔幻妖怪等。其中有些母题为日本动漫所独有的元素,后来被其他国家的文化资源借用,比如《圣斗士星矢》中的不死小强、《十二国记》中的穿越元素、《银魂》中的吐槽恶搞、《夏目友人帐》中的“百鬼夜行”模式、《闪灵二人组》中的男男CP组合,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都是由日本漫画首创的流行元素。从类型上对日本漫画做划分,大体可以分为热血少年系、少女系、竞技类、暗黑系、治愈系、推理悬疑类、机甲系、校园类、搞笑类、后宫系、同人系等,这些类型之间的划分只是大体的区隔而并不绝对,存在相互交融的可能。比如《银魂》既是少年系又是搞笑系,《魔法少女奈叶》既包含美少女元素也是战斗机甲类作品,《网球王子》既有美少年的元素也是运动竞技类作品的代表,《名侦探柯南》表面上看属于推理类,事实上还涉及很多历史文化的知识元素。
一 少年漫画:由竞技、机甲、热血到小清新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的投降,使日本民众开始反思战前那些涉及日本武士道精神、军国主义理想的连环画如何诱导了思想,最终使自身陷入了战争的痛苦与泥沼。因此,在日本无军备力量的制裁之下,漫画杂志中出版武士故事被视为违法,柔道、空手道、相扑等运动也属于违法之列。对竞技体育的禁止后来被麦克阿瑟将军解除,因为他认为竞技体育是一种释放军事与战争压力的方式。于是在政策的导向之下,彰显运动之魂的少年漫画层出不穷。从日本国民最爱的棒球、相扑、围棋,到日本人并不擅长的足球、篮球、网球乃至赛车、钓鱼,一应俱全。竞技体育类的少年漫画满足了争强好胜的大和民族无法发展军备的心理需求,在体育场上的胜利同样也是民族精神的彰显。《足球小将》《灌篮高手》,长达几百页,每一次动作都被一一分解,惊心动魄的布局、速度线、状声字以及模糊并透视缩短的身影,都将漫画效果推向高潮。体育漫画流派有自己的程式:看似没有天赋的选手(失败者或者小孩),经过师父的严格训练,最终取得胜利。这种的漫画程式不仅用于竞技类漫画,还用于武术漫画、科幻漫画,也用来描述商界的成功以及强权政治,甚至用于讲述漫画行业自己的故事。
除了战争主题之外,日本少年漫画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并无二致,都擅长使用关于英雄、青春、动作、竞技并略带喜剧色彩因子。由于战败国的身份与原子弹给日本国民带来的深重的痛苦,日本漫画很少涉足真实的战争场景,而将触角延伸至虚拟的外太空。机甲类漫画作为日本少年漫画中的一类代表,集中地代表了这种心态。机甲(Mecha)就是巨型机器人,这种形象被日本动漫中反复使用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其一,日本拥有先进的科技,但无法运用于军事力量的建设中,将先进技术用于虚拟想象中赢得战争,是获得心理认同的一种方式;其二,日本人种属于东亚,从形体和力量上逊于白种人,因此使用机械装甲武装战斗者与身形体力更强者比拼,符合日本人对战争的合理想象。科幻类漫画(science fiction)中与外太空的战斗是日本漫画的重要母题,巨型机器人被视为操作者身体的有效延伸,当日本的科技向微型电子产品发展的时候,日本的漫画科学家们却大量制作巨型机器人。《铁甲万能侠》及其系列产品预示着影响迅速、成长急速的一种亚文化——高科技机械文化(Mecha)的产生。《超时空要塞》、《高达》、《机动警察》和其他一些身着紧身衣的变形机械人的传奇故事诞生了。最初在动画电影和电视上出现,后来被改编为漫画作品。在高科技和高文明时代,跨星球的、模糊过去和未来、使人和机器相互依赖和制约,成为日本漫画作品中的一类特定情节。对机甲类漫画的个案分析见下文。
除了竞技与机甲之外,少年漫画中最核心的元素还是团队精神、不懈努力、升级打怪。《少年JUMP》等一些杂志的受众群由6岁到60岁,其卖点凝结为一些价值观,诸如友谊、坚持还有赢得胜利。经历了战后的萧条与重建,日本人不断在少年漫画英雄中寻觅鼓舞和慰藉。少年不仅指男孩,还指“纯净的心灵”,这些普适内核成为日本动漫的优秀元素。在90年代的中国,漫迷最早接触到的日本漫画产品大多是热血少年系,如《圣斗士星矢》《幽游白书》《通灵王》等,后来的《海贼王》《犬夜叉》《死神》也大多归于此类。对热血少年系的个案分析见第三章第一节。
随着日本漫画的多元发展,治愈系漫画成为受众获得正能量的精神源泉。治愈系原指音乐中能够安慰人心、曲调悠扬的作品,后被动漫文化转借而成为热词。治愈系有温情治愈系、纯爱治愈系、文艺治愈系、暗黑治愈系、励志治愈系等多个分支,整体呈现出风格优雅、节奏缓慢,饱含鼓励、小确幸,也有淡淡的物哀,最终能够达到温暖人心、净化心灵的效果。《蜂蜜与四叶草》《虫师》《夏目友人帐》可以视为治愈系的代表。对治愈系作品的个案分析见下文。
二 少女漫画:由青春恋情到现实指向
少女漫画最初由男作家创作,主要指以身处少女期的12—18岁的受众为主要观众对象的动漫,泛指拥有少女情结、人物美型、唯美纯净的恋爱型的动漫作品。男作家试图以女性的视角对描绘恋爱故事,大多纯真而美好,画风干净唯美,作品多由美型男女构成,以浪漫美好的爱情故事为蓝本,编写成符合青春期少女恋爱幻想的作品类别。其中典型的作品包括《彩云国物语》《凡赛尔玫瑰》《尼罗河的女儿》等,也包括一些层次比较丰富,但也被归为少女漫画的作品,如《NANA》《魔法少女奈叶》《蔷薇少女》等。日本有专门的少女漫画期刊,如小学馆刊发的《少女COMIC》,集英社旗下的《RIBON》等。
一方面,女性漫画家的崛起是少女漫画盛行的必备条件。
男性作家创作的少女漫画是以男性的视角构建女性的所思所想,带有天然的刻板印象与局限性。20世纪70年代,是日本漫画界最发达的时期,大约有400名女性漫画家活跃在舞台之上。“随着上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日本的70年代乃是性别角色及人们对两性的固定形象发生重大转换的时期,以至于以男女性别对调为主题的作品也在这一时期接踵登场。”[3]女性漫画家不但丰富了少女漫画的内容与形式,更重要的是,少女已经不再是女性作家唯一的读者群体,其他社会群体也纷纷追捧女性漫画家的作品。
与中国的历史相近,日本历史上有类似母系氏族的时期。到了德川幕府时期,深受中国儒家文化浸润的日本开始萌发男尊女卑的思想,到1868年明治天皇时期实施对妇女更加严格的奴役政策。少女漫画的最初蓝本顺应了时代的需要,贤良淑德、在家从父、出嫁随夫的传统女性占据主流。随后,描绘欧洲奢华生活或者魔法少女的形象又成为流行趋势,《美少女战士》《宠物小精灵》并称这一时期的代表。到了20世纪70年代,女性漫画家开始大放异彩,五位出色的独立漫画家形成了一个团队,分别为:荻尾望都(Moto Hagio)、池田理代子(Riyoko Ikeda)、大鸟弓子(Yumiko Otori)、竹宫惠子(Keiko Takemiya)、山岸凉子(Ryouko Yamagishi),并称为“花之24年组”。这些女漫画家不仅在故事内容、绘画技法上,更在时空表现与隐喻内涵上实现了突破,虽然女漫画家是由少女漫画起家,但并未止步于少女系的恋爱动画,而最终走向了哲学、历史、科幻与写实主义。“许多女漫画家的爱情故事已经超越了优质的罗曼史、简单的男女相遇的爱情公式,她们令人惊叹的精美、可爱的插图画面常常掩盖了她们想要探讨的东西:关于认同、自我接纳,关于个人成功、家庭和友情,关于变老和死亡等问题。”[4]女漫画家笔下的纯净美好的少年爱作品成为日本动漫中的经典母题,而高鼻大眼的“魔法少女”也成为全球广泛认可的日本动漫形象代言人。
作为日本女性作家的矢泽爱(Ai Yazawa),自1985年起创作了诸多优秀的动漫作品,如《近所物语》《下弦之月》《天堂之吻》,而令这位女性漫画家蜚声全球的是她在1999年创作的《NANA》。《NANA》的同名电影与动画作品都掀起了“娜娜热”,这部漫画讲述了两位同名的女性大崎娜娜与小松奈奈在东京寻找梦想的故事,以其精致的画风、深刻的现实指向、人物性格的鲜活而备受追捧。
另一方面,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女性漫画形象值得探究。
虽然大部分少女漫画是出自女性漫画家之手,但是依然很难摆脱男权社会之下,女性被凝视、被观看的视角。不仅仅是少女漫画,其他的以女性为主要受众的小说、影视作品不约而同地再造女性的世界观,不断重申获得男性之爱的重要性,以及幸福的来源是与所爱的男性结婚生子。之所以使用“再造”或者“建构”这类的词语,是因为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在社会教化中养成的。因此,大部分少女漫画无法逃脱恋爱故事的窠臼,正如中国影视剧中流行的一类“宫斗剧”一样,几乎都由各类美丽的女性构成,但是却是在男权视角下言说的。表面上看是以某几个女性的人生历程为主线,却将女性的幸福与特定男性的宠爱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是“伪女性视角”。少女漫画也呈现出此种特征,在故事构成上常以某位女性的经历为线索,女性充当了主角,但是评判女性、审视女性的视角通常在男权社会的价值观中构建。
社会性别论通常用社会性别(gender)来代替通常所使用的生理性别(sex),更加强调在社会活动中所逐渐形成的性别观念。在当代日本,由于全龄动漫社会的打造,适合不同年龄、性别、阶层的动漫产品异常丰富,如幼儿动漫、少年动漫、少女动漫、成人动漫、白发动漫等。动漫的影响力如此之大,动漫中所呈现出的性别观念会潜移默化地塑造或改变社会公众的性别观念。斋藤美奈子(Mainaiko Saito)在《红一点论——动画 特技 传记中的女性形象》(1998)中将女性出场人物分为四个类型:魔法少女——在父母的庇护下一边梦想着结婚一边沉迷于游手好闲的少女(神圣的母亲候补队),红色战士——被男人包围且一边工作一边物色老公的年轻女人(神圣的母亲候补队),邪恶女王——没能嫁人且无法成为母亲的在工作中的老姑娘(非神圣的母亲资格者),神圣母亲——在背后支持丈夫和子女活动的理想女人。以上四类女性形象在日本动漫作品中多有体现,但界限并不明显。事实上,单纯讲恋爱的动漫番剧并不算多。简单来讲,着重单纯描写恋爱以及描写婚姻情感的动漫并不占据主流,所以导致这种类型的动漫存在的数量也较少。为了确保制作出来的动漫迎合更广大的受众,在恋爱番中往往会加入战斗/科幻/游戏/校园/日常/异能等多种元素。而这些元素的增加又会降低对“恋爱”的描写,直至最后可能这些其他元素占据主流,而“恋爱”“婚姻”这种剧情的描写反而变成次要要素。
以恋爱元素为主线(相对主线)是容易见到的。但是以婚姻、结婚为题材的作品较少。原因如下:恋爱这个题材是相对轻松的,受众范围广(十几岁至几十岁的受众都可以接受),容易产生共鸣,是绝大部分作品可以融入的元素。而婚姻、结婚等题材,相对严肃,对20岁以下甚至更高年龄层的受众来讲,这个题材是很难产生共鸣的。除非不可避免,一般动漫作品很少会以“追求婚姻”为主线。比如魔法少女类型,《刀剑神域》中的“亚丝娜”与男主“桐人”的关系是相对平等的,严格意义上讲,应该算是“互为幻想结婚”的类型。根据原作以及衍生作品分析,女主“亚丝娜”的确会产生要与男主“桐人”结婚的想法,甚至在虚拟世界中,他们还有了孩子。但是局限于这部作品偏科幻/游戏的设定,对这种情感的描写并不明显。《RE: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中的“拉姆”和男主的关系更类似于“仆人”与“主人”的关系。很难得,这部作品对主要角色之间的感情描写非常到位。由于这部作品掺杂了“穿越”“异世界”“魔法”“冒险”等元素,导致人物之间的感情也很复杂。“幻想结婚”这一剧情是在动画第18集,主角“486”在产生逃避现实的想法后,雷姆在安慰男主的时候,对其的表白中体现的。
红色战士的类型更多地存在于“少女向”的漫画中,这些一边被男性包围,一边工作、一边物色老公的女性形象广泛存在。比如《银仙》中的市松小雏、《会长是女仆大人》中的“鲇泽美咲”、《吸血鬼骑士》中的玖兰优姬等都是红色战士的典型代表。社会性别形象在日本动漫发展的几十年中发生了很大的转向,比如在机甲类的科幻动漫中,《宇宙战舰大和号》和《机动战士高达》中红色战士类女性角色非常多,到《新世纪福音战士》那里女性突破了上述四种类型,体现出更多的自主性。
被边缘化的非婚主义者的角色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出现变化。如果说早期的动漫作品中,老处女之类的角色是被嘲弄、被厌弃的形象,那么在晚近的漫画中,已然发生变化。漫画《我不受欢迎,怎么想都是你们的错!》中的“黑木智子”被中国网友称为“丧女”,在日语语境中“丧女”指不受欢迎的、没有恋爱经验的女性。“高中一年级的女学生,不擅长与人交涉,和其他人进行对谈时常会没来由地紧张不知所措。常常对于他人、事物有着较反面、愤世嫉俗的批评想法,也是个标准的丧女。”
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类型在日本动漫中也多有指涉,大多出现在一些日常番中,如中国受众耳熟能详的《蜡笔小新》中的“野原美伢”(小新的母亲)、《哆啦A梦》中的“野比玉子”(野比大雄的母亲),以及漫画《海螺小姐》中的女主角。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的新番《小林家的龙女仆》中的“托尔”,这个角色算有着完善的家庭主妇的条件,但是又不像传统的“家庭主妇”角色那样,她更类似于“女仆”这种角色的设定。所以在日漫中“女仆”与“家庭主妇”这种类型的角色往往存在相似的设定。
事实上,在1998年以后的20年间,日本动漫中的性别角色发生了很大的转型。动漫流行语言中的“草食男”和“肉食女”的出现,代表着跨性别(transexual)现象的存在。女性想象逐渐突破了上述四种类型,而呈现出多元化的走向。如《夏目友人帐》中的夏目玲子、《名侦探柯南》中的妃英理、《XXX Holic》中的壹原侑子、《银魂》中的月咏,都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动漫女性形象的角色属性。
对少女漫画的个案分析见下文关于矢泽爱作品《NANA》的内容解析。
三 多样漫画:全龄漫画王国的打造
日本文化史学家吴智英认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走向中,以直接叙述、故事性强的小说逐渐被抛弃,成人漫画则填补了这一空白。明治维新之后的知性小说家群体,倾向于放弃线索清晰的叙事,而转而描写细腻丰富的人物心理,在日本大正时代形成了日本现代文学中“私小说”的传统,作者成为了小说的亲历者与主人公。这种文学类型在中国现代文学的郁达夫一派中也有明显的体现。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文学形式已经失去了活力,读者们,包括知识分子读者,都已经对这类小说失去了兴趣。而此时,漫画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表达形式,因为漫画能把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戏剧化”。[5]漫画包含并超越了小说的所有表现形式,从低俗、粗野的讽刺小说到高雅、抒情的小说应有尽有。
(一)青年漫画与成人元素
日本漫画之于日本国民,正如好莱坞电影之于美国民众,承担起替代性满足的功能。日本漫画接受中的“代际矛盾”存在于二战时期老一辈的日本人不理解子女成年还在阅读漫画的习惯。而许多战后高峰期中出生的孩子,在孩提和学生时代就与漫画相伴,是名副其实的漫画一代。也正是他们对漫画的兴趣和对媒体的尊重,刺激了漫画的成长和改变。伴随着岁月的流逝,战后五六十年代阅读漫画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开始进入职场。出版商们为长大的漫迷精心打造“青年”(seinen)漫画,这一时期,漫画的主要读者慢慢转型为坐着地铁上下班的白领一族。无论是在狭窄的公寓里,还是在远程上下班的旅途中,漫画都为上班族打造了独有的精神空间。每一章漫画的时间都被精心设置过,和地铁两站之间的空隙完美对接。漫画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成熟人士关心的人物形象,如武士、骑士、屌丝、情场老手与翩翩公子,漫画变身为诸如职场关系、恋爱指南的教科书。
在青年漫画中,暴力和性的元素很快出现。这也成为很多国家将日本漫画视为洪水猛兽的原因。各种形式的国家和地方法规对漫画做出规定,漫画的内容也有各种专门机构和群众团体对之实行监控。公众也可以对认为有害的漫画进行投诉,这是一种通用、便利的监控方式。不堪入目的作品被列入政府青年政策措施的黑名单,并被当地议会禁售。与很多国家禁售含有色情内容的漫画相悖,被西方政府称为“道德放纵”的日本漫画是否应该为犯罪率负责是值得商榷的议题。日本漫画的发行量是美国的十倍,相反,日本的暴力犯罪率是美国的十分之一。由此,漫画疏导论开始抬头,即漫画排遣了人本能对暴力与性的想象,从而维护了社会秩序。
日本的成人漫画影射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失业、高利贷、黑社会、政府与财阀腐败、日美关系与民族主义,甚至描绘了原子弹、地震频发给普通民众带来的深重苦难。生命的脆弱感、高科技的发达与荒漠的自然环境成为日本成人漫画中的一大主题,诸如《阿基拉》《新世纪福音战士》《天咒》《风之谷》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描绘了灾难场景与环境主题。
(二)非主流的个性漫画
与很多国家漫画家编制作品是为了出版盈利不同,日本漫画界还活跃着许多非主流的个性漫画。并非所有的日本漫画都能高速度、大规模出版,有些作品没有固定的读者,也远离商业化的路径。在漫画出版的边缘地带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同人志作品与个性昭彰的漫画家。在西方,这样的一些漫画家会被标为“地下作家”,因为他们无视主流读者群,或者对主流读者群毫无兴趣,只顾彰显自己的风格。然而,在日本,“主流”与“地下”漫画之间的界限变得相当模糊,这是由于漫画出版业的规模庞大和持久,喜爱漫画的人群庞大,即使是不被看好的漫画家,其作品也有受众群体,甚至会逐渐获得商业的成功。因此,在维持生计的压力之下,这些个性漫画家依然不断创造出风格独特的作品。
被称为“日式恐怖”的漫画类型就是其中之一。与欧美恐怖元素更多地以暴力和血腥为展示方式不同,日式恐怖常建立于心理恐怖的基础上,在细节上刻画细思极恐、脊背发凉的不寒而栗的恐怖感,常与科幻、重生、不明现象入侵、梦境相关。日式恐怖成为世界范围内饱受关注和争议的元素,长发贞子、咒怨中的小孩都是恐怖片爱好者的惊喜与噩梦。楳图一雄(Kazuo Umezu)被誉为“恐怖漫画第一人”,被推理小说家绫辻行人(Ayatsuji Yukito)尊称为“神”,其代表作品《上帝的左手、恶魔的右手》描绘了虚拟和现实的交织,亦真亦幻;伊藤润二(Junji Itou)的短篇漫画《长梦》《鱼》《富江》《漩涡》等作品刻画了压抑与绝望的气氛;岩明均的《寄生兽》则偏重科幻恐怖。这些漫画的同名电影如《上帝的左手、恶魔的右手》《富江》《寄生兽》都早已被搬上大荧幕,其中“富江”与“贞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恐怖标签。黑暗系(Darkness)与恐怖漫画有近源关系,是自文学兴起以来而衍生的一种文体,血腥杀戮、暴力美学等非主流元素也出现在日本漫画之中。关于暗黑系的个案分析见下文。
漫画中的超现实主义则为另外的一个派别。柘植义春(Yoshiharu Tsuge)是典型的非主流漫画家,其作品《沼泽》《螺丝式》被称为日本漫画的实验作品。这类作品人物造型夸张、情节天马行空、意象支离破碎、结局悬而未决,使读者深深困惑却又为之着迷。柘植的个性漫画为自己绘画,不为迎合订单、不赶最后期限,也不是在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泛泛之作。从超现实主义的寓言故事,到对日常生活痛苦的反思,到他用第一人称讲述消失之地的旅游见闻,他的漫画让人感到深刻而亲切。就像他的漫画人物“无能的人”一样,柘植的弟弟也是一位漫画家,但常陷入困顿的处境最终自杀,柘植义春对漫画爱恨交织,曾几次放弃漫画,但他的那些带有实验性的作品广受赞誉。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之衷爱有加,并被频繁地改编成意味深长的电影和电视剧。如今,他的同行和晚辈视他为灯塔,一座用漫画媒介来表现反思、内省自我生存意义的明亮灯塔。
在日本漫画的巨大宝库中,同人志也是其对世界漫画贡献的特殊文化产品。最无拘无束的漫画主题也许可以在数千种地下漫画“同人志”中找到。日文的字面意思是“同人杂志”,但“爱好者杂志”也许是最佳翻译。同人志本身是供同好间交流的作品,一般分为延伸型故事与原创故事两类,后因为大受欢迎而走上公开出版的路径,甚至有的同人志作品比原著还要流行。这种作品和杂志并非粗制滥造,其中有些制作极其精美,像是昂贵的艺术家的作品,既有限量版也有大规模重复印刷。漫画爱好者杂志和漫画爱好者俱乐部自20世纪60年代初便随处可见,影响力更广的“同人志”盛会于1976年在一个东京小型聚会上创立,与会者是数百名漫画家和他们的读者,这些读者称它为“comiket”,即“comic market”(漫画市场)的前身。现在的“Comic Market”每年在东京举办两次,已经成为全世界御宅族的节日,持续吸引各国数以百万计的动漫爱好者参与,是日本最大的公众集会。有关comic market的调研报告见附录。
(三)“大漫画”概念与全龄漫画王国的打造
“大漫画”的概念指漫画不仅仅是精神文化的产品,更是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漫画是信息传播生动、有效的途径,漫画家们能够巧妙地寓教于乐、有效地劝导公众。早期教育和学校里的课本都可以采用漫画的形式,不同年级的教科书与复习资料都可以用漫画的形式来增强理解力。无论是插花、茶道、厨艺、钓鱼还是高尔夫,漫画可以提供各种知识。反过来看,早在二战时期,受军国主义影响的漫画家就曾创作漫画小册子,用以离间美国军队中不同种族间的关系;1995年,制造地铁毒气袭击事件的奥姆真理教,以连载漫画的小册子招揽众多信徒;1999年的日本民族主义者们也借助图画小说作为他们的宣传媒体。漫画元素在国外的使用也值得关注,2002年日韩世界杯,不论是英国广播电台的体育频道还是赞助商阿迪达斯都不约而同地选择足球漫画来打广告。伦敦的英国国家歌剧院有了宣传漫画,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官方指定产品巴克斯顿矿泉水也选择漫画来做广告,巴黎市长甚至用漫画向他的市民祝贺新年。漫画已经不仅仅是小众群体喜爱、交流、消费的文化产品,也成为广告商、体育赛事、政府机构、交通指南、医疗急救等各大系统争相追捧的风格元素。由此可见,漫画在说服公众上有着极强的视觉冲击力、浅显易懂,故被各行各业广泛使用。
二战后的日本现代漫画,经过五十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全龄漫画王国,正如手塚治虫所言:漫画就是这个时代的空气。从黄口小儿到耄耋老人,从青春期少女到上班族男性,无不从漫画中寻找到快乐与认同。儿童可以在漫画中寻找到快乐的童年时光,少年在友情和恋爱的漫画中收获成长,青年男性借助漫画寻找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成年男性在漫画中关注社会问题。比如女性漫画,阅读这类漫画可以了解到关于如何处理严肃的家庭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在青少年教育中父母难以启齿的“性教育”可以从中找到,中年危机中的“解惑阿姨”也由女性漫画承担,对于如何交往男朋友、处理婆媳关系、解决离婚困扰、获得幸福生活都可以从中找到建议。“正如伊藤所说的,妇女们不仅可以在这样的漫画中得到积极的情感宣泄和精神洗涤,她们还可以从中得到切实的建议。”[6]《可怕的婆媳》《付账》《感觉年轻》等漫画期刊已经是成为婆婆和奶奶的女性们也阅读的女性漫画,到20世纪90年代,有60多种各色各样的女性漫画供选,其中囊括爱情、成长、心理健康、生活指南与职场经验。最终,漫画伴随着一个人从孩提走向暮年,读者和漫画的关系可以持续终身,漫画犹如家庭成员,与人们一起慢慢变老。正如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歌野晶午的《樱的圈套》一书,使用叙事诡计的方式描绘了老年人的责任心、勇气和恋爱,令人拍案叫绝。同样,“银发”漫画中打破了以往漫画中对老年人顽固、邋遢的刻板印象,可以看到对长者充满敬意的描绘。与诸如《黄昏流星群》《退休了,没有老板,不用工作》等讲述老年人恋爱和干劲的作品一样,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简单地划分为智慧老人或古怪的老傻瓜,而是体现出白发族的浪漫与敏锐。随着全世界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银发漫画”也会拥有越来越多的潜在读者。总而言之,“漫画的七个时期”贯穿了人的一生,从摇篮到坟墓的每一个阶段,成为终身的陪伴与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