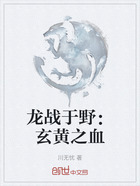
第4章 观道交锋,初试文气
寒冬渐深,崖山城被素白的雪花覆盖,儒学馆内却格外温暖。卜子敖已在馆中修行近半年,《大学》烂熟于心,文气运转也逐渐纯熟。每日清晨,他会在院中练习“存思守正“之法,感受体内那股越来越清晰的力量。
这一日清晨,卜子敖刚完成早课,就见言述匆匆而来,面色凝重:“子敖,收拾行装,随我出一趟城。“
“出城?去何处?“卜子敖疑惑不解。
“颜师有令,命我带你前往三十里外的青峰山。“言述压低声音,“齐国有位名儒将在那里与各家道统弟子进行一场'观道会',师兄弟们都已先行一步。“
“观道会?那是什么?“
“简言之,就是各家道统弟子聚在一起,相互切磋,交流道法。“言述解释道,“这类聚会在乱世中并不常见,各家道统多有嫌隙,能坐在一起和平交流实属不易。此次观道会,齐国名儒孟轲主持,以'仁政王道'为题,意在探讨治国之道。“
卜子敖心中一动:“为何颜师要我也去?我才疏学浅,恐怕难堪大任。“
言述微微一笑:“颜师说你天资不凡,且有特殊机缘,此行正好开开眼界。况且,这次观道会上,据说会有不少年轻俊杰,你正好与同辈交流切磋。“
言述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还有一事,可能与你胸前的异象有关。颜师说,你体内的文气与常人不同,似有特殊感应。此次观道会上,诸家道统齐聚,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线索。“
提及胸前胎记,卜子敖不由自主地抚摸胸口。这些日子来,随着文气的增强,那对盘绕的龙形图案也越发鲜明,有时甚至会在他运转文气时微微发光。这种异象,连颜师都感到不解。
卜子敖收拾简单的行装,跟随言述出了城。初雪过后的崖山周边,银装素裹,分外妖娆。两人沿着山路前行,路上言述不断为卜子敖讲解各家道统的特点和观道会的注意事项。
“观道会上,各家道统各有所长,互有克制。“言述语重心长地说,“儒家重礼重德,以中和为本,但在直接对抗中,往往不如兵家的霸道杀伐、法家的律令锁禁来得干脆利落。不过,我们的优势在于'文气浩然',能正心明道,抵御邪祟,还能以'言出法随'之术,影响规则和人心。“
卜子敖认真聆听,将这些要点牢记于心。
经过半日跋涉,他们终于来到青峰山脚下。只见山脚下已搭建起数十顶华丽的帐篷,帐篷前旗帜招展,各家道统的标志清晰可见。来自各国的修士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谈甚欢。
“那边是我们儒家的营地。“言述指向一处朴素的营帐,上面悬挂着一面绘有“文“字的旗帜。
刚走近儒家营地,就有几名身着儒服的弟子迎了上来:“言师兄!“
言述一一见礼,随后介绍道:“这位是我崖山儒学馆的师弟卜子敖,初入道途,请诸位师兄多多照应。“
众人纷纷向卜子敖行礼。其中一位年约二十出头、面容清秀的青年走上前来:“久闻贤弟大名,久仰久仰。“
卜子敖一愣,自己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农家子,何来'大名'之说?
那青年看出他的疑惑,解释道:“贤弟初修文气,便能感悟'存思守正'之妙,且体内文气纯净无比,这在我辈中实属罕见。颜师早有书信来往,提及贤弟之事,我等皆是心生敬佩。“
卜子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师兄过奖了。我不过是运气好些罢了。“
“我叫杨文简,齐国稷下学宫的弟子。“青年自我介绍道,“听闻贤弟来自农家,能在短短半年内有如此成就,实在令人钦佩。“
两人相谈甚欢,很快便熟络起来。杨文简对卜子敖十分友善,不仅向他介绍了在场的各家道统代表,还告诉他许多观道会的隐秘规则。
“观道会表面上是各家道统和平交流,实则暗藏较量。“杨文简低声道,“每次会后,都会有不少道统弟子改投他门,这也是各家争夺人才的方式之一。所以,待会儿若有人挑衅,切莫轻易应战。“
正说话间,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只见一队身着黑衣的修士大步走来,为首的是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脸上刻着狰狞的刀疤,眼神锐利如刀。
“那是谁?“卜子敖问道。
杨文简面色微变:“秦国的兵家弟子,为首的是赵国降将李牧的弟子岳铁山。此人好勇斗狠,最擅以军阵煞气压人,你见了他,最好绕道而行。“
卜子敖点点头,目光在那群兵家弟子身上扫过。他能感觉到,这些人周身散发出一种凌厉的气息,如同出鞘的利剑,让人不寒而栗。
太阳西落,营地上燃起了篝火。观道会正式开始了。
一位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老者走到中央,高声宣布:“诸位道友,欢迎参加本次观道会。老夫孟轲,今日有幸主持这场盛会。观道会的宗旨是各家和平交流,共商治国安邦之道。大会共三日,第一日各抒己见,第二日切磋道法,第三日总结议定。今日已晚,请各家推举代表,发表对'仁政王道'的见解。“
随着孟轲的宣布,各家道统纷纷派出代表上前发言。法家的代表强调“以法治国“,推崇严刑峻法;道家的代表则主张“无为而治“,顺应自然;墨家的代表提出“兼爱非攻“,反对战争;兵家的代表则认为“国强民安“,唯有实力才能保卫国家......
轮到儒家发言时,杨文简作为稷下学宫的代表走上前去。他侃侃而谈,阐述了“仁政王道“的核心理念——以德治国,以民为本,强调君王应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达到大同世界的境界。
卜子敖专心聆听,不时有所感悟。各家道统的理念虽然不同,但都有其可取之处,如何取长补短、兼容并包,这正是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
就在各家发言接近尾声时,岳铁山突然站了起来,冷笑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诸位口若悬河,说得天花乱坠,不如来点实在的!老子不信这套'仁政王道'的鬼话。真要治国,还得靠实力说话!“
他转向杨文简,挑衅道:“小儒生,你们儒家总说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实际上呢?齐国有你们这些儒生辅佐,不还是打不过我们秦国?“
杨文简不慌不忙:“岳兄此言差矣。治国之道,不在一时胜负,而在长久之计。秦国虽强,但残暴之政难以长久。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废话连篇!“岳铁山不屑一顾,“既然你们儒家这么厉害,那我倒要领教领教!“
说着,他周身突然爆发出一股凶悍的煞气,如同实质性的黑色雾气,向杨文简压去。“来,接我一招'军魂煞气'!“
在场众人纷纷色变。这岳铁山竟然在观道会上动手,实在太过分了!
杨文简面对袭来的煞气,不退反进。只见他脚踏八卦步,手捏儒家印法,口中朗诵《论语》:“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随着他的诵读,一层淡淡的白光在身前形成屏障,那股凶悍的煞气竟然被缓缓化解。
岳铁山见一招不成,冷哼一声,双手结印,体内煞气暴涨:“军阵锋芒,给我破!“
这一击更为猛烈,杨文简的文气屏障开始出现裂纹。他额头冒出汗珠,显然有些支撑不住。
就在危急时刻,卜子敖体内的胎记突然剧烈发热!他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几步来到杨文简身旁,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只凭本能开口道:“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这是他最近刚刚熟记的《论语》篇章,虽然修行尚浅,但此刻他竟然感到胸中有一股磅礴的力量涌出,汇入话语之中。他的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仿佛带着某种神奇的力量。
令人震惊的是,随着他的诵读,那本应薄弱的文气屏障竟然开始逐渐加固,岳铁山的煞气攻势被一点点化解。
“这......“岳铁山面露惊异,显然没料到一个看起来如此年轻的儒生,能有这等本事。
卜子敖也同样震惊。他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文气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转,而胸前的双龙胎记更是剧烈跳动,仿佛有生命一般。
孟轲见状,及时出面调停:“好了好了,观道会重在交流,不在争斗。两位小友都展现了不俗的道行,不如就此罢手如何?“
岳铁山不甘心地收回煞气,冷冷地看了卜子敖一眼:“有点意思。不过,等到真正的战场上,我看你们这些儒生还能不能靠几句话抵挡千军万马!“说完,转身离去。
杨文简长舒一口气,感激地看向卜子敖:“多谢师弟相助,若非你及时出手,我恐怕要在众人面前出丑了。“
卜子敖摆摆手:“这也是凑巧,我也不知为何能有如此效果。“
“不是凑巧。“言述不知何时来到他们身旁,眼中闪烁着惊喜的光芒,“子敖,你可知你方才展现的,已经是初步的'言出法随'之术了吗?这在你这个修行阶段,是极为罕见的!“
孟轲也饶有兴趣地走了过来,仔细打量着卜子敖:“这位小友是......“
“弟子卜子敖,崖山儒学馆学生。“卜子敖恭敬行礼。
孟轲点点头:“难得,难得。如此年纪便能初窥'言出法随'之门径,天资不凡啊。“他转向言述,“言贤侄,可否让我单独与这位小友谈谈?“
言述欣然应允。
孟轲带着卜子敖来到一处僻静的亭子,坐下后细细端详他:“小友,不妨露出你胸前的胎记给老夫一观。“
卜子敖一惊:“您怎么知道......“
孟轲微微一笑:“老夫在你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异于常人的气息,再加上方才你运转文气时,胸前隐有光芒透出,不难猜测。“
卜子敖迟疑了一下,随后解开衣襟,露出那对盘绕的黑白双龙胎记。
孟轲眼中闪过一丝震惊,随即又恢复平静:“果然是它......“
“前辈可是知道些什么?“卜子敖急切地问道。
孟轲沉思片刻:“这胎记,老夫在古籍中曾有所见。相传乃是'玄黄之血'的象征,与天地大道息息相关。“
“玄黄之血?那是什么?“
“玄,天也;黄,地也。玄黄之血,象征天地之精华。“孟轲解释道,“相传上古时期,天地初开,玄黄二气交融,孕育出无数生灵。而其中最精纯的一缕气息,化作'玄黄之血',流转于世间。拥有这种血脉的人,天生与大道亲近,且对各家道统都有特殊的感应能力。“
卜子敖心中震惊,这些话与他平日的感受竟然如此吻合!每当他专心研读儒家经典,胎记都会有所反应,而今日面对兵家煞气,竟然也能本能地作出抵抗。
孟轲继续道:“不过,这种血脉有利也有弊。利在于你可以更容易理解和掌握各家道统的精髓;弊在于你很难在单一道统上达到极致。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你能找到一条融合之路,开创属于自己的道。“孟轲意味深长地说,“这条路极为艰难,前无古人,后或无来者。但若成功,或许能超脱现有道统的局限,达到一种全新的境界。“
卜子敖心中震动,没想到自己的身世竟有如此玄妙之处。
“不过,老夫建议你暂时不要声张此事。“孟轲语重心长地说,“如今天下大乱,道统之争日益激烈。'玄黄之血'若为人所知,恐怕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你且先在儒家安心修行,打好根基,日后再考虑融合之事。“
卜子敖郑重点头:“弟子明白,定当谨记前辈教诲。“
两人又交谈了许久,孟轲为他详细讲解了儒家更高深的心法,以及如何在道统之争中自保的要诀。临别前,孟轲还赠予他一枚古朴的玉佩,说是可以在危急时刻提供一定的庇护。
夜深人静,卜子敖躺在帐篷中,久久不能入睡。今日所见所闻,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原来他体内流淌的,竟是传说中的“玄黄之血“,难怪他总能比常人更快领悟儒家义理。
他想起孟轲所言的“融合之路“,不禁心生向往。如果真能融合各家道统之长,开创一条新路,那该有多么美妙?但这条路必定充满艰险,且不知从何入手......
次日清晨,观道会进入切磋道法环节。各家道统的弟子们分组交流,展示自己的所学。卜子敖本想低调行事,却发现不少人向他投来好奇的目光,显然昨晚的事已经传开了。
“卜师弟,这边来。“杨文简招呼道,“今日有各家道统的入门心法展示,你正好可以开开眼界。“
卜子敖点点头,跟着杨文简来到一处空地。只见场地中央,已经有数名不同道统的弟子在比试。有道家弟子施展符箓之术,引动风火;有墨家弟子展示精巧的机关造物;还有法家弟子演示“律令锁禁“,让一片区域瞬间变得规则井然。
“真是大开眼界啊。“卜子敖感叹道。这些道法,在平日根本无缘得见,如今能亲眼目睹,实在是难得的机会。
正看得入神,忽然一个阴恻恻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就是你,昨晚挡了我师兄煞气的小儒生?“
卜子敖转身一看,只见一名身着黑衣,面色阴鸷的青年正冷冷地盯着他。
“这位师兄有何指教?“卜子敖拱手问道,尽量保持礼貌。
“我叫秦无情,是岳师兄的师弟。“黑衣青年冷笑道,“听说你不过入门半年,就能抵挡兵家煞气,我很好奇你究竟有何本事,不如咱们切磋一番如何?“
卜子敖心中一凛,这分明是来找麻烦的。他正想拒绝,却见言述从远处走来,微微摇头。卜子敖明白师兄的意思,观道会上拒绝切磋,有失风度,但也不能轻易应战。
他沉吟片刻,决定迂回应对:“秦师兄盛情,在下感激不尽。只是在下修为浅薄,恐怕难以领教师兄高招。不如这样,我问师兄一个问题,若师兄能答上来,我便认输如何?“
秦无情一愣,随即冷笑:“好啊,你问吧。“
卜子敖沉思片刻,故作正经道:“请问秦师兄,'无情'二字,当作何解?“
“这还不简单?“秦无情不屑道,“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用兵之道,就是要无情,只有无情,才能在战场上取胜。“
卜子敖点点头:“师兄此解甚合兵家之道。不过,在下却有不同见解。“
“哦?“秦无情挑眉,“你能有什么见解?“
卜子敖缓缓道:“子曰:'人无情,不立。'情者,人之本性也。无情非人,有情则仁。秦师兄称自己'无情',却又与人交谈论道,这本身不就是情之所致吗?“
他的声音不大,但字字珠玑,隐含文气。不知不觉间,他已经将初步的“言出法随“之术融入言辞之中,试图以理服人。
秦无情面色微变,似乎被这番话触动。他本想反驳,却发现自己竟一时语塞。因为卜子敖的话确实戳中了他心中的某个柔软之处。他自幼习武,被灌输“无情才能成事“的理念,却也曾在深夜怀念家乡,思念亲人......
“好一个巧舌如簧的儒生!“秦无情最终冷哼一声,“今日算你走运,改日再来领教你的本事!“说完,转身离去。
杨文简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子敖,你太厉害了!那秦无情可是兵家新秀,平日里横行霸道,谁都不放在眼里,没想到竟然被你三言两语就给说退了!“
言述走上前来,眼中满是赞许:“子敖确实进步神速。方才那几句话,不仅有理有据,还暗含'正心明志'之术,能让对方不知不觉受到影响,这已经是儒家中阶修为才能掌握的本领了。“
卜子敖谦虚地摇摇头:“纯属侥幸罢了。不过是借用了孔子之言,再加上一点微末道行。“
实际上,他心中也相当震惊。方才与秦无情对话时,他仿佛有一种奇妙的感应,似乎能看透对方内心的波动,因而能说出最能触动他的话语。这种感应,是之前从未有过的。
不知是否与昨晚孟轲所说的“玄黄之血“有关?
观道会接下来的日子里,卜子敖尽量保持低调,但仍然有不少人来找他交流。他发现自己确实如孟轲所言,对各家道统都有某种直觉上的理解。无论是道家的“无为自然“,还是法家的“严刑峻法“,甚至是兵家的“军阵煞气“,他都能在短时间内领会其中要义,并找到与儒家思想的共通之处。
这种理解不是表面的知识积累,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共鸣,仿佛这些道理本就刻在他的骨子里,只需一点引导就能唤醒。
观道会的第三天,孟轲主持了总结发言。他高度评价了各家道统的贡献,同时也呼吁大家在乱世中保持初心,不要被权势所诱惑。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孟轲语重心长地说,“如今周室衰微,天命流散,各国争霸,道统相争,正是大分之时。但道之所在,终将汇聚。希望各位道友都能坚守本心,寻找那真正的大道所在。“
会议结束后,各家道统的人开始陆续离去。卜子敖与新结交的友人一一道别,尤其是与杨文简约定日后常有书信往来。
返程途中,言述对卜子敖说:“这次观道会,你收获不小啊。“
卜子敖点头:“确实大开眼界,也更加明白了什么是道统之争。“
“不仅如此。“言述意味深长地说,“你还得到了孟大儒的赏识,这可是不小的机缘。我看得出来,他对你格外关注,想必是看重你的潜力吧。“
卜子敖没有提及孟轲与他谈论“玄黄之血“的事,只是含糊地点点头。他心中已经有了决定——先在儒家打好根基,同时暗中了解其他道统的精髓,为将来可能的融合之路做准备。
回到崖山儒学馆,颜师召见了卜子敖,详细询问了观道会的经过。当听说卜子敖能够初步运用“言出法随“之术时,颜师欣慰地点点头:“不负所望,不负所望啊。“
他沉吟片刻,对卜子敖说:“从今日起,你可以开始学习《中庸》了。此篇乃是儒家进阶必修,讲述'执两用中'之道,对你接下来的修行大有裨益。“
卜子敖恭敬接过颜师递来的竹简,心中充满期待。
当夜,卜子敖静坐书房,细读《中庸》。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他不仅仅是在读书,而是在有意识地以“玄黄之血“的特殊感应能力,去体会《中庸》中所蕴含的道理。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随着一句句经文的诵读,他心中的玄黄气海愈发清晰,道种也愈发茁壮。而更令他惊讶的是,在气海深处,那两条龙形虚影似乎更加鲜活了,如同随时可能苏醒的沉睡巨龙。
卜子敖不知道,在观道会之后,他的名字已经开始在各家道统中悄然流传。儒家新秀,言传法随,玄黄异象......各种传言纷纷扬扬。而在更高层次的道统争锋中,一些有心人也开始注意到这个崖山儒学馆的年轻弟子。
风起云涌的时代,每一个微小的变数,都可能影响整个局势的走向。卜子敖,这个怀揣“玄黄之血“的农家子弟,即将在这场波澜壮阔的道统之争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道种生长,异象渐显。一场更大的变局,已然悄然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