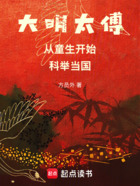
第10章 知县临学
城南隅三所社学按年岁先后顺序,方原所在社学排在第三位,而社学又称小学,故也可称呼该学为城南隅第三小学,嗯,不加实验。
成化六年九月末,吴先生带领所有童生在社学大门外列队恭候,原因无他,本县父母官李知县即将到来。
方原站在吴先生身后,跟虎子嚼舌根:
“还是当官好哇,咱们眼巴巴等着,就为在县老爷面前奉承一揖,人家说诸生辛苦,你还得觍着脸道大老爷更辛苦。嘿嘿~”
虎子听得憨憨直乐,再往后的方存义小心提醒道:“叔,你小声点,可别被先生听到,又要罚你了。”
方原当即闭上了嘴,这倒不是因为侄子的提醒,只因他看到身前的吴先生,身子微微起伏,明显憋着怒气呢!
得,适可而止,见好就收。
方原干咳一声,一本正经道:“虎子,公共场合可不敢乱说话,咱要安心恭候长官大驾。”
虎子困惑地挠了挠头,我也没说话呀?
此时一个头戴小帽,身穿青衣,腰系青丝带的皂吏从远处小跑而来,一见吴先生就道:“县尊片刻便至,先生仔细些。”
吴先生致谢,忙整理衣冠不提。
很快两个腰间束着红布织带的皂班衙役开道,一顶软轿缀后,由远及近。
大明朝开国那会儿,太祖皇帝的规矩多,文武百官无一人敢乘轿。
可如今世道变了,在京官员三品以上许乘轿,而在外天高皇帝远,连代天子巡狩的巡按御史都从最早的骑驴改骑马,再改乘與轿,身为百里侯的一县之主,在其辖区内乘个轿自然不在话下。
当脚夫稳稳落轿,轿帘掀开,头戴乌纱身穿绣着鸂鶒青袍的知县老爷,笑眯眯地走了出来。
吴先生赶紧携童生们躬身行礼,口称:“社学蒙师吴中梓见过县尊。”
知县名唤李唯清,天顺八年进士,将近四十的年纪,白面短须,生得富态,此时和颜悦色道:“何烦师生辛苦迎候。”
吴先生忙道:“县尊乃本县父母,提调学校,诸童生尊师重道,迎候自是应该。”
李知县笑意更浓:“吴先生客气了。”
吴先生口称不敢:“在下后学末进,不敢当县尊‘先生’之称。”
吴中梓一介儒士,不过秀才功名,在李知县正途进士面前只能算后学晚辈,哪敢称先生。
几番推辞,直到李知县呼其为小友方才作罢。
吴先生道:“请县尊移步学堂训教童生。”
李知县笑着应下,在吴先生的指引下,踏入社学大门,紧随其后的便是一同跟来的礼房老吏。
待众人都入了学堂,坐在讲案前的李知县环视童生,语含深情道:“我太祖高皇帝在位之时,诏令郡县兴举学校,作养贤才与图治道,故乡社有校,郡县有学。汝等今日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全赖国朝如天之德,诸生当思向学之心,以全报效之意,方不负皇恩浩荡。”
这句开场白,李知县在县学给秀才们讲过,也给其他社学童生们讲过,可谓万金油之言,屡试不爽。
刚说完这话,李知县下意识去拿茶盏饮茶润嗓子,可城南隅第三小学学舍简陋,吴先生平日粗茶淡饭,根本没有好茶招待。
只见白瓷盏中茶汤并不鲜亮,一望便知是次等绿茶,此等劣茶他李知县是不会喝的。
放下茶盏,李知县颇为不悦的干咳一声,一旁的吴先生心知怠慢,面露尴尬。
哪知此时,最后一排的方原却自顾自鼓起掌来,啪啪声,突兀而清脆。
李知县循声望去,指着后排鼓掌之人问道:“你这童生何故拊掌啊?”
吴先生看着鼓掌的方原,顿时头大,这臭小子非得给他整出点事才甘心,忙从旁辩解道:
“此子平日尊敬师长,友爱同学并无失礼,许是初听县尊教导,失了方寸,才会拊掌赞和。”
鼓掌古称拊掌,自古就有称赞之意,可正式场合长官训话时,却无拊掌的习惯,方原突兀的鼓掌难免失之轻佻。
李知县却不悦道:“本县要听他讲。”
吴先生擦擦额头细汗,给了方原一个凌厉的眼神,提醒他答话一定要慎重。
方原起身行礼道:“回禀县尊,适才小子听县尊讲起太祖皇帝兴举学校之语,追思历代先皇教化之德,心神激荡之下,只觉一股爱国忠君之情油然而生,故而拊掌直抒胸臆,望县尊恕罪则个!”
吴先生暗暗给方原点了个赞,还是你小子会鬼扯。
李知县看着还留着总角的少年,乐道:“你唤作何名,几岁年纪?”
方原身板挺直,朗声道:“回县尊的话,小子名叫方原,已满十四岁。”
李知县轻捋颌下三缕短须,赞道:“少年人朝气勃发,很有精神嘛!那你说说看我祖宗朝为何要广兴教化?”
方原道:“我朝疆域辽阔,人口众多,若教化不行,则风俗浇漓,四维不振,是故民行不可不修。而立社学以教幼,明宗法以尊老,孝悌崇廉立不言之化,五伦之出于性者又淑于教,则悖逆邪佞之病不驱自除!因此小子窃以为我朝历代先帝以风化之事体大,所虑千秋将来,而严饬力行。”
李知县心下暗自吃惊,这小童生对朝廷的政策理解透彻啊,将来若不做官那就可惜了。
“你教的?”李知县朝吴先生投去探寻的目光。
吴先生脸上挂满笑容:“晚生平日也就教他读经解惑而已,如何教得他这般见识。”
“那就是其父所教了!”李知县喜道,“令尊何人呢?”
方原正色道:“先考讳鸿。”
先考乃是对亡父的尊称,李知县今年刚到任自然不知道方鸿名号,另一侧的礼房老吏低声道:“方鸿方先生乃本县饱学之士,县学廪生,天顺五年病故。”
李知县颔首,感慨道:“果然家学渊源!”
几番问话,李知县对方原起了兴趣,温言道:“方生四书可曾通读?还未学经吧?”
方原回道:“《四书集注》都已读过,至于五经,我今从吴先生习《书经》。”
五经分为《诗》、《书》、《礼》、《易》、《春秋》,虽都需要通读,可科举考试却只需专擅一经便可。
通常童生七岁开蒙,年纪渐长便可习四书,再长至十四五岁便可专经。
但社学蒙师素质良莠不齐,开蒙教育各社学都相差无几,至习书专经阶段,则为分水岭,非名师不能释疑解惑!
童生想要考入县学,要么削尖脑袋往有名师坐镇的社学、蒙馆里钻,要么游学外邑访求名师。
李知县眼前一亮:“已读《书经》?倒是好学,吴小友,可曾安排童生讲书,若未曾,我便出题由他来讲一篇。”
吴先生心中暗喜,还好早有安排,忙道:“那便有劳县尊考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