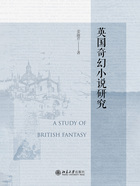
序
舒伟
四川外国语大学姜淑芹教授的学术论著《英国奇幻小说研究》即将出版,这是她历经数年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成果,可喜可贺。笔者曾在扬子江和嘉陵江这两江环绕的山城读书和工作,只要说到四川外国语大学,头脑里自然会浮现“川外”这一熟悉的称谓,也必然引发对往事的回忆。那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在缙云山下一所重点大学攻读英语文学硕士研究生。那时候研究生招生规模较小,外语系一届往往只招一到两个研究生,导师和各门课程的任课老师加在一起,远远超过研究生人数。在此情形下,我们对同处山城的四川外语学院同一时期入学的,同一专业方向的研究生的情况自然有所了解,对他们的专业学习和论文写作的动向也较为关注。就在我们专注于啃读莎士比亚剧作和诗作,以及现代派作品如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到灯塔去》《海浪》时,有些出乎意料地发现川外的研究生在做外国儿童文学研究,而且做得有声有色,形成了不小的气候。要知道那时候儿童文学的学科研究对于我们绝对是新鲜事物。不久四川外语学院就成立了外国儿童文学研究所,而且创办了登载外国儿童文学作品译文和研究、评论文章的刊物。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事实上,这一翻译和研究行为已经载入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的史册 —— 1986年,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专门委托四川外语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在重庆召开“外国儿童文学座谈会”,会议的中心议题包括如何进一步开展外国儿童文学的研究和译介工作、当今外国儿童文学的新趋向、如何建立和加强我国与外国儿童文学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1 1987年,川外外国儿童文学研究所编辑的《外国儿童文学研究》开始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说实话,当时读到这份刊物的文章时内心不由得生出强烈的羡慕之情,须知当年能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的研究生,甚至老师,少之又少。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川外的研究生在毕业之后去了南方的城市工作,相关的研究也逐渐沉寂下来。设想一下,如果四川外语学院外国儿童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一直持续不断地坚持下去,那么完全有理由相信,川外一定会成为国内学界外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以及比较儿童文学研究的重镇。
如今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姜淑芹教授的不懈努力之下,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多语种儿童文学翻译与研究创新团队已经组建起来,并且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翻译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淑芹在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时完成的学位论文是对罗琳“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综合研究,体现了她对于英国儿童幻想文学的学术关注。如今即将出版的这部书稿是对前期研究的深度拓展。她在进行英国儿童幻想文学的学术考察和研究期间,还致力于翻译英国儿童幻想文学名作,包括苏珊·库珀的《黑暗在蔓延》和C. S.路易斯的《纳尼亚传奇》等幻想文学作品,以及伊娃·伊博森、菲利普·普尔曼、艾米·斯帕克斯的作品等,为国内幻想文学研究者提供了阅读文本。
从人类文化史看,幻想文学的传统源远流长。放眼历史时空,人类先民在谋求生存发展的过程中无不怀有拓展自己经验视野的深切愿望。这种愿望自然成为推动人类驰骋想象,竭力感知和认识自身和世界的原动力,同时也催生了各民族的早期幻想文学:神话叙事。尽管所有古代神话故事都不需要得到现代意义的证实或确认,但它们不失为早期先民们在观察、探索自然世界以及现实体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有意义的幻想性叙事,从而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著名科幻小说作家和学者布赖恩·奥尔迪斯将现代幻想文学划分为两极,一极是追求思考和批判的分析性作品,以英国作家威尔斯(1866—1946)为代表;另一极是梦幻性的奇异幻想作品,以《人猿泰山》的作者美国作家巴勒斯(1875—1950)为代表。 20世纪以来,托尔金(1892—1973)创作的《霍比特人》及《魔戒》系列为梦幻性叙事传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尽管幻想文学同源异流,具有共同的想象与虚构特征,但不同的类型,以及预设了不同读者对象的作品往往同幻异旨、同工异曲,具有出自不同创作意图的艺术追求。事实上,“幻想文学”范畴宽泛,包罗甚广,可以统称所有同源异流,相似相近的非写实性文学类型,例如在成人文学语境中,有梦幻叙事、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科幻小说、成人本位的政治童话及新童话叙事,等等;而从幻想叙事文类看,可以划分为童话小说、奇幻小说和科幻小说,等等。由此可见,在缺乏具体语境的情况下,“现代幻想文学”这一称谓显得尤为模糊,指向性并不明确。正如布赖恩·奥尔迪斯指出的:“幻想文学(fantasy)作为一个描述性术语具有难以把握的广泛通用性是众所周知的。”2 有鉴于此,在幻想文学传统和现代幻想文学演进历程的参照下,根据特定国家的文化历史语境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幻想文学进行系统考察是很有必要的。当然,这也表明这种历史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现象的考察和研究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开放性的,包容性的。
《英国奇幻小说研究》采用社会历史文化批评阐释与代表性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针对与奇幻小说研究交叉最多的儿童文学和童话研究语境,对现当代儿童和青少年本位的英国奇幻小说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这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坚持“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该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这一哲学原则。作者紧紧抓住对于有自觉意识的英国奇幻文学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因素和作家作品现象,根据基本史实进行探讨,做出阐释。与此同时,作者对各重要时期的时代特征与文本的文学表达特点进行提炼总结。例如,对于维多利亚时期出现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奇幻小说,作者梳理了初期的奇幻故事如何脱胎于现实主义叙事,巧妙地走向幻想的奇境世界,描述主人公如何从现实世界穿越到一个奇境世界的经历。在叙事形态方面,往往设有一个连接现实世界与奇境世界的入口,在叙事内容上主要表现主人公进入新世界后惊奇、迷惑、恐惧,最后获得成长的历程。其主要代表作品就是引领维多利亚时代儿童文学黄金时代的两部“爱丽丝”小说。
法国文艺理论家罗杰·加洛蒂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了具有很大影响的论著《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全书用三章的篇幅,分别通过对画家毕加索、诗人圣琼·佩斯和小说家卡夫卡的创作特征的阐释,从绘画、诗歌、小说三个艺术领域论证了现实主义创作的“无边”的疆界。加洛蒂对现实主义的当代形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未来发展做出了新的阐释。在论述卡夫卡的文学创作特征时,加洛蒂指出,相较于毕加索这样的立体派画家通过自觉的颠倒次序来揭示最寻常事物的内在诗意,卡夫卡通过颠覆和改变日常生活现实的面貌来呈现对生活的真实内心感受。小说家对这个世界的材料进行了重新组合,创造了一个幻想与现实并存的文学世界。如果说莎士比亚的艺术是面对自然的一面明镜,那么卡夫卡的艺术依然是一面镜子,只不过映照的是扭曲变形的现实。镜中的世界仍然是现实的映像,是另一种“真实”。事实上,卡夫卡的文学世界与“爱丽丝”小说的奇境世界是相通的。爱丽丝进入兔子洞和镜中世界后遭遇了难以理喻的荒诞事件和滑稽可笑的人物,领略了各种逻辑颠倒的奥妙和玄机。作为整体构架上的梦游“奇境”,“爱丽丝”小说也是具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意涵的梦境叙事。正如罗伯特·波尔赫默斯所言:通过创造“爱丽丝”文本,卡罗尔“成为一个我们可以称为无意识流动的大师。他指明了通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道路”3。波尔赫默斯进而论述道:“从卡罗尔的兔子洞和镜中世界跑出来的不仅有乔伊斯、弗洛伊德、奥斯卡·王尔德、亨利·詹姆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弗朗茨·卡夫卡、普鲁斯特、安东尼·阿尔托、纳博科夫、贝克特、伊夫林·沃、拉康、博尔赫斯、巴赫金、加西亚·马尔克斯,而且还有20世纪流行文化的许多人物和氛围。”4 在此,笔者还要对两部“爱丽丝”小说原著书名的中译文表明一点看法。首先,《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仙境”一词是否妥当,很值得商榷。考虑到原著的基本内涵和中西文化对“ wonderland”的认识差异,笔者认为用《爱丽丝奇境历险记》比《爱丽丝梦游仙境》更为准确。我们知道,这部小说的前身是根据作者在1862年7月为利德尔三姐妹口头讲述的故事而完成的手稿《爱丽丝地下游记》,定稿后于1865年出版。研究者注意到这两部小说蕴涵的“陷入沉沦和困境的世界”这一主题,它们还呈现了许多后来体现在20世纪的文学大师笔下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因素,尤其是与弗兰茨·卡夫卡作品相似的噩梦般的困境,在一种由悬疑重重和荒诞无解等因素构成的梦幻迷宫中出现的存在主义和黑色幽默因素,如何遭遇荒诞的敌对力量,和那些异己、异化的强大力量。而从精神分析学的视阈看,跳进兔子洞就进入地下世界,这个地下世界既是地球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神秘莫测的未知世界,象征着进入难以理解和应对的无意识领域。波顿执导的影片还告诉观众,当爱丽丝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她曾经掉进过同一个兔子洞,并且把“地下世界”(underland)误听成了“奇境世界” (wonderland) 。由此可见,“奇境历险”或“奇境漫游”要比“梦游仙境”更接近原著的书名及其内涵。
对于20世纪初期的英国奇幻小说的时代语境,本书作者进行了这样的提炼: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人们焦虑情绪的加剧,全社会呈现出一种心理迷惘的状态。奇幻小说领域表现出一种对顽童形象的狂热和对于回归家庭的渴望,作家通过营造时光停滞的怀旧感来化解现实的压力。在艺术表现形式上魔法被引入现实世界,从空间穿越扩展到时间穿越。作者对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奇幻小说的解读也是颇具阐释力的,指出这一时期是现代奇幻小说的“史诗时代”,那些代表性作品通过回到远古神话构建史诗来重建信仰,帮助人们克服战争创伤,凝聚国家力量,重塑民族身份。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的主要历史背景就是冷战。冷战思维下的英国社会延续了50年代的恐惧与创伤,但更多地表现在心理层面。苏珊·库珀的《黑暗在蔓延》系列与托尔金的《魔戒》史诗传统一脉相承,回到更具英国性的亚瑟王传奇资源中寻找力量,开创了心理魔法模式。戴安娜·琼斯则开启了奇幻小说的解构之风,颠覆惯常认知,通过主人公发现自己内心隐含的力量。作者对于20世纪90年代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的英国奇幻小说创作特征进行了阐述。这是英国奇幻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家包括菲利普·普尔曼和J. K.罗琳。通过对两位作家作品的细读和阐释,作者揭示了当代英国奇幻小说的质疑与颠覆精神,以及开放与包容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当然,研究有自觉意识的英国奇幻小说的发展历程和创作特征,从社会历史文化批评视野进行考察和阐释并非唯一途径;而且对于英国奇幻小说的界定,如何区别儿童本位与非儿童本位的作品仍然存在着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与此同时,如何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和阐释相关命题,仍然存在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场域。此外,对于童话故事在维多利亚时代对于英国人的重要性,对于为什么文学童话在维多利亚时期成为一种深受欢迎的书写形式,还可以给予一定关注。因为文学童话对于维多利亚英国的文化想象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是童话故事对于维多利亚人的精神意义和吸引力,另一方面是创作文学童话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众多作家用以抵抗精神危机的文学武器。从总体看,作者采用的社会历史文化批评视野能够有效地体现唯物辩证法批评武器在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的阐释力。这正是这部学术著作的价值所在。期待淑芹教授在外国儿童文学研究和中外儿童文学比较研究领域贡献出更多成果。
1 王泉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第464页。
2 B. Aldiss and D. Wingrove, Trillion Year Spree: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London, The House of Stratus, 2001, pp. 5-6.
3 Robert M. Polhemus, “ Lewis Carroll and the Child in Victorian Fiction”,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ed. John Richett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 p. 579.
4 Robert M. Polhemus, “ Lewis Carroll and the Child in Victorian Fiction”,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ed. John Richett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 pp. 581-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