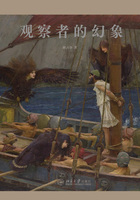
第3章 眼睛与光芒
事物的存在作为一种现象,并不是恒常地存在于那里的。作为现象之物,作为瞬间的存在样态,事物倾向于将自身隐匿。漫长的诗歌史向我们透露了这一秘密。这是诗与事物的双重秘密。而诗人的努力即在于坚持不懈地着眼于使事物呈现自身,迫使事物进入在场。
在场之物便是诗人眼中的诗意之物。
迫使事物在场,这就是给予空间,给予使事物得以显现的场所。这意味着去除遮蔽,给予光芒。
眼睛即是光芒的给予者。在词语中它已被恰当地称为“眼光”或“目光”。
事物的存在,取决于我们以何种目光去看它,去迎接它。
但诗意之物并非是主体以一种浪漫情调附着上去的,诗意是生存世界本身的蕴含,正像它同时包藏着祸心,包藏着爱、疯狂、暴力、苦难与死亡一样。遗忘了诗意之物,我们甚至不能理解凡俗之物,不能理解世界。叙述语言的诗意化,也是生存世界的诗意呈现。
语言的诗意化即意味着语言的感觉化,或感觉化的语言。但归根结底,语言的知觉功能只是体现了人的某种敏锐的目光。正是清新的目光才使表达它的语言知觉化了。仿佛语言本身成了某种知觉器官,成了一种目光。因之,诗意并非什么缥缈之物,它就置身于纯朴的感性和清新如初的感觉经验中,置身于如雨后的晨曦一样的目光中。一部作品或一种生存状况之所以说没有诗意,就是因为它可体验的感受经验是匮乏的。
可体验的感觉经验在这里指的是某种原初的、清新的、永远作为第一次的感受,是语言对处于瞬间状态的事物的感性的呈现,而不是指对于恒常之物的指称、描述。
事物似乎是一直在那里的,这并不保证人们确实经验到了它,也不担保事物进入了在场。人们的感官确实终日受到许多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拥有了经验。事物可能被认为是司空见惯的,可能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的。感官经验的日常化与功利化也可以使它迟钝与麻木,以至感官只为我们提供一些生物性的经验,诸如冷热、痛痒、饥渴、危险……这些实用的指令。一般而言,日常感觉只为人们提供一些关于事物的效用性的观念。只有在某种瞬间,事物才作为存在的现象或在场之物被我们瞥见。
诗人总是相当敏感地将事物进入存在的瞬间感性地呈现出来。这不仅仅是一种氛围或背景的描述,而且是存在的现身情态,是事物汇入世界、世界进入事物的时刻,是存在的完满的时刻。因此作品对事物的描述不再只是介绍人物的环境,而具有了文学的根本功能,即使存在显现的努力:
树木的呼吸赶走了群山,山中的道路像一缕青烟在晃动。天暗了;橙子飘浮在空中;听得见最低弱的回声;一枚落叶或一只歌唱的小鸟能在沉睡的原野上激起十分深沉的回响;梦妖在灵魂中醒来。[4]
显而易见,这里的语言中包含着一种眼光,一种清新得令人眩晕的眼光。无论你说这是一种想象,或一种比喻也好,都没有掩住这种强烈的、新鲜的视听经验。完整的经验。没有把它从事物中剥离掉,没有隐去目光,也没有隐去目光之所见,事物的在场。尽管这些事物(比如山中的路)是永存的,可经过表达的事物却更像是瞬时即逝的。
从一般地描述、指称事物,到对事物的瞬间状态的感性呈现,有着遥远的距离。只有把握到了事物的瞬间状态,才可以说把握到了存在的瞬间或存在的现象,把握到了生存的时机。心灵才真正地经由事物并在事物中进入了世界。这也许是因为,心灵同样地只在某种瞬间才算是活着。事物的进入在场使人获得了一种面对面的在场。
事物的恒常状态并不能担保这一点。事物并不总是能够呈现出世界。山上的一条道路总是在那里的,但“像一缕青烟在晃动”的山路只存在于某个瞬间。暮色渐浓,隐去或融解了那些树木上悬挂着果实的枝条,但是火焰一样的橙子却格外醒目,它们飘浮在空气中。这样的对事物的呈现与注目,既有蓬热意义上的事物即诗学的真义,也有普鲁斯特式的“重现的时光”或空间诗学。自从我读到这样难忘的话语,它就带动着它的景物在我的眼前晃动、飘浮,使我自己也曾看到过的事物最终被真实地看见了。难道真是这样?如帕斯所言——
我没用眼睛看见:话语
是我的眼睛。我们生活在名字中间;
那无名的事物
仍不存在……
看见世界就是拼写它。
话语之镜:我在何处?[5]
如果人们不能直觉到事物的瞬间状态,那么人们既不能找回事物世界,也无处寻觅已逝的时光。因为重现的时光并非一种对等的均匀的时间连续体,过去的时光是由一些瞬间的事物构成的疏密不等的空间。如果没有被心灵铭记和被眼睛直观的瞬息的事物,时间过去就是一片空白或黑暗。
在诗人和艺术家那里,对事物的瞬间状态的呈现无非是,在捕捉到事物 —世界的形象的同时,也总是同时呈现了事物的声音、光影、色彩和气息。这里还有一只清新的耳朵,仿佛在这话语中,听觉才被唤醒,并警觉起来,因为世上那些值得看、值得聆听的事物并不喧嚣,它需要我们的目光和听力敏锐。
我们总是在宁静和回忆的气氛中才重新看见或听见它们:使人心中充满孤寂之情的落叶的最后的划动,树叶或鸟鸣在田野中激起的深沉的回响,风吹过树木和夜空在身体深处唤起的颤动,以及娇弱的呻吟,光脚丫子拍打雨水的咕叽声,马车在泥水中滑动的声音……灯、烛光、星,蓝得让眼睛发花的天空,雨水中像蘑菇似的游动的雨伞,长了青苔的树荫地……麦穗儿的香味,豌豆的清香,阴雨天河边水草的腥气,女性身子散发的香味,从躯体内部放射出的光芒,仿佛不是被月光照亮,而是她们照亮了月亮和隐约的夜色中的一切……这一切存在着的形、色、声、味,形成了我们生活的氛围,它们是存在之光,温存、迷蒙而又广阔、坚实,使我们心底生出对存在的信赖和亲密。它们像无形的、无边的抚爱存在着,在我们身边,也在我们内部。
什么是我们的生活世界?正是这无法说出名堂的一切事物。无论怎么样,它们存在着,一会儿光亮一会儿变暗的大地、草场、村舍、果园或庄稼地,叶片上的光影与露水,尽管看起来是那么靠不住,可是它们存在着。这对于我们是宝贵的。由于它们瞬间的呈现,由于它们的永恒存在,我们分享到一种甜蜜、清新的生命感觉,它在我们身上激荡起神秘的欢乐之情。对我们来说,事物的瞬间状态的呈现就像是永恒的诺言。我们感到自己莫名其妙地受到了祝福,预感到拯救可能就来自豌豆的清香,一把黄雨伞,一朵花瓣上的露水或一个女人的颈背。我们整个无着落的世界,孤独、疏离的事物仿佛围绕着这个形象建立起来。这些事物犹如我们的感情在其中燃烧的火焰的形式,像凡·高的向日葵和丝柏那样,是情感的火焰的形式。
然而我们敢说自己真的会看吗?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是盲人吗?
我们的目光早已丧失了其清新性,我们的目光总是被什么晦蔽着。事物总是在那里,因而看仿佛已是一个惯例式的行为。但是司空见惯就是一种“不见”,就是一种盲点。司空见惯就是一种不在场,一种事物和人的双重隐匿。
绘画(如同关于物的诗篇一样)的历史为我们保持着、创造着真正的“看”的传统。画家总是在观看中训练自己的眼力和目光。
可见的世界存在着的恰恰是“可见性之谜”,而绘画,恰如梅洛-庞蒂所说的,是对千古之谜的“可见性之谜”的颂扬,也是对可见性之谜的表达。
眼光,如同阳光那样是使事物显现出其轮廓与形态的一种力量。在可见物的世界上,影响着事物的瞬间性存在状态的是光芒。一方面,这种光来自太阳、天空和云层;另一方面,在人这里,影响着事物存在样态的就是目光。这样两种光造成了事物的难以捉摸的可见性。
可以说,画家对事物的研究、凝视、观察与呈现,既是对外部光谱的研究,也是对目光自身、对“看”的一种探索。在拉斐尔前派的画家那里,对光的探索成了对大自然的奥秘作出表现的焦点。天空与光芒在康斯太勃尔的作品中,就像光芒在但丁的《神曲·天堂》中的那种作用一样,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光芒就像是尘世事物的精神性,对光的呈现拯救了平板无奇的自然。地平线之上的天空与光芒是对地上的事物的一种召唤,并赋予其生命力。湖泊、水流、移动的云层和闪光的树叶在灵性之光的影响下发生着抑制不住的运动。光的存在带来了这么一种观念:他眼里所见的一切不一会儿就又会发生变化。可以说,这样的画家不是把一些事物搬上了画布,而是把一小会儿时间、把存在的一个瞬息移上了画布,移往了永存的可见性之中。他们在云影、光柱、虹、阵雨、草叶、湖面……上寻求着对光的表现。正像透纳在谈到鲁宾斯时所说:“我指的不仅仅是虹本身,还有那含着水滴的阳光,清新、消失的冻雨,以及雨后天晴时的灿烂辉煌。”[6]在这里,云、水滴、叶片或空气的颤动,都是光的交响。
在印象派画家的另一种闪烁的目光中,物质的事物几乎消失了,它的坚硬的轮廓被同样闪烁的光点融化了。他们摆脱了光的流贯一体即化除了整块色彩,事物仿佛散发为闪烁的、流动的光点,事物悬浮在密集的光点的空白处。它使我们重新“看见了”事物。我们在这种“看见”中,已经经历了一种“看”的创造。这种目光取消了对深度的追求,而停留在反射的、漂浮的、流动的事物的表面。因此,皮埃尔·理查说,印象派画家似乎终于使物质得以透出空气,这种闪烁的光点或目光实际上以某种方式切开了事物的昏暗,它是“一种横向的透明”[7]。
在此之后,在塞尚那里,物体不再被反射光覆盖,不再消失在它与空气的关系中,梅洛-庞蒂说,物体“好像从内部被暗中照亮了,光线从物体上面自己放射出来,由此造成了固体性与物质性的印象”[8]。
物就是光芒。从知识上说,色也就是光谱。
每一件物体,都是光,那是本源的光所生成的光。玛瑙、宝石和我们周围的自然之物都是光,它们从自身内部呈现出自己,即照亮自己。
在神秘的遐想者的眼光中,一切上升的、垂直的物体都是生长的光芒,树木都是流向天空的火,一朵向日葵即是烧焦的光芒,“在火苗的花园中”。
光芒是在一条梦游之河边
一块呼吸的石头,
光芒,一个伸展的少女,
一捆破晓的黑暗之麦束……[9]
光芒就是那使事物在黑暗中显现出来的东西,是视看的一种条件。而每一事物的形式就是它自身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