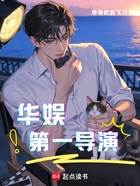
第2章 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前世,1975年出生的顾晨在文学系得到硕士学位后,便留校任教。
从北电文学系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文学系主任,主讲世界电影史、电影大师研究、编剧理论与技巧和经典电影赏析等课程,排过几部话剧,也出过几本书。
其中一本经过删减后,被定为各大艺术院校的教材,综合类高校中文系、传媒学院里的一些专业,也用这本教材。
相信你能大概看出来,他属于学院派性质,根正苗红。
但不像后来转当导演,拍出《烈日灼心》《追凶者也》等电影的同事曹宝平。
顾晨教学二十多年,并未拍过一部长片,主要觉得没什么真正地需要调动生命经验去表达的东西。
感受倒是有一些,但不值得拍成电影,发个朋友圈,或者跟朋友一起喝两杯,就能缓解。
直到2025年,父母相继故去,自己也得了一场重病。
好转后,天命之年的顾晨正式筹拍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电影主要根据哲思散文《我与地坛》改编,也结合了顾晨的一小部分亲身经历,以及艺术再创作。
最终,这部横亘近四十年历史的传记片,于2027年5月,在第8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斩获金棕榈和影帝两项大奖。
该片成为继《霸王别姬》后,第二部获得戛纳金棕榈的华语电影,男主宝强也成为继葛大爷和梁生后,第三位获得戛纳影帝的华人男演员。
重磅奖项+1,宝强+段龙的人气加成+2,,原作家的国民度+3,完全不枯燥,甚至看过就忍不住泪崩的故事+4,自来水观众的口口相传+5,同档期其余影片的衬托+6,猫眼的发行和营销+7……
天时,地利,人和,顾晨的这部处女作顺势定档暑期后,比当年的《我不是药神》还猛,获得了40.6亿的票房,成为2027年暑期档票房冠军。
在年度票房排行榜上,则是亚军,仅次于大年初一上映的《流浪地球3》。
经此一战,顾晨在业内的知名度和地位都直线上升。
接下来两部片子,也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众多影企的追捧,和众多男女演员的崇拜下,顾晨迅速迷失在了商业浪潮里,开始渐渐忘记了自己是谁,从哪来,要到哪去。
其实,最开始,顾晨还是挺有底线的。
但有个常年走下坡路的影企,想邀请他执导一部电影,被他礼貌拒绝了。
第二天一早,他发现自己躺在酒店,身旁还有这家影企签约的一个00花。
为了保住颜面,他理所当然地妥协了,让这家影企成了投资方之一,一部片下来,让他们小赚了两个亿。
之后,顾晨彻底放飞自我,像大多数业内高层一样,奉行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三不准则。
在某读书综艺当天录制完成后的傍晚,他吃了点药,好让自己有精神和体力,跟主演自己第四部片子的女演员之一(某个当红小花),仔细研读刚刚完成的剧本。
但或许是药效过猛,顾晨彻底失去意识前,对那个世界的最后一个印象,是一个老男人在给他喂药。
这人胡子拉碴,头发潦草,眼睛小小,皮肤很糙,但他是谁来着?
这档读书综艺的嘉宾?我处女作的文学顾问?还是比我大十几岁的忘年交?啊,记不太清了。
也好,从混沌中来,到混沌中去,他慢慢闭上了双眼,五十余年的人生化作无数镜头,一一在眼前浮现。
第一次上学抱着母亲的腿不撒手,第一次取得全校第一被鼓励,第一次跟初恋女友在河边拥吻,第一次被父亲说自己长大了……
第一次登上学院讲台,第一次到了陪父母去看病的年纪,第一次操办自己家人的葬礼,第一次拍摄自己的处女作……
也正是这次走马灯,让顾晨看到了自己之前看到过,但完全不曾注意的细节。
不知在黑暗中飘荡了多久,顾晨才幽幽醒转。
一睁眼,便是报志愿,他喜极而泣,父母还说他这么大的人了,激动个什么。
顾晨抹抹泪,没说话。
报好志愿,来到卫生间镜子前,看到熟悉且陌生的面容,又偷偷掐了自己一把后,他才确信,自己的确是来到了十八岁。
他看着镜中的自己发誓——
各位必须看到我!而且是早三十年看到我!
“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的情况,绝对不能再发生!
全球票房排行榜上,99%都是好莱坞影片的情况,绝对不能再发生!
所以这次,他没选文学系,而是悄悄地选了导演系。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母亲还教训了他一顿,父亲也少见地说了他两句。
顾晨也乐意听着,甚至还笑嘻嘻的。
须知,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能被父母骂,说明你还小,还被爱,还有退路,不知是多少人可望而可不得的心愿呢。
顾母没法,也只好由着他去了,毕竟年轻人的时间宝贵,不能白白复读浪费一年光阴。
再说,学院的导演系也不错。
这年头,大导演是有行政级别的,而且还是文艺工作者,说出去也有面,不会给他们家丢脸。
-----------------
从办公室出来后,顾晨乐乐呵呵向前走着。
说实话,不怪老郑谨慎,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情况嘛。
就拿这时候来说,国内的电影制片厂讲究论资排辈,厂标有限,胶卷有限,资金有限,各种资源都有限。
一般北电摄影系的学生毕业后,想掌镜当摄影师,都得熬上好几年。
拍片这种事,无论如何,都轮不到他这种二十多岁的小年轻。
第五代导演里,家庭“成分”不好,只能卖血买相机的张导就不说了。
出身电影世家的壮壮、诗人这些人,也都是在三十出头才得以拍摄长片处女作,没有长辈眷顾的一谋,还要再晚几年。
1986年,已经三十六岁的一谋,主演《老井》时那叫一个玩命,全程配合、琢磨,跟吴厂长一起讨论怎么拍更好。
为了演出孙旺泉在井下奄奄一息的感觉,他好几天没有吃饭。
最终,获得金鸡电影节、百花电影节和东京国际电影节的三个影帝,受到该片导演,也就是西影厂的吴厂长大力赏识。
之后,他才得到《红高粱》的拍片机会。
但即便这样,消息一出,西影厂也炸了。
厂里有老人直接给吴厂长跪下,搞道德绑架。
说壮壮、诗人这些导演系的高材生能拍就就算了,姓张的那小子丫一摄影系的,还是旁听生,“走后门”进去的,掌镜才几年啊,凭什么当导演?
我比他大这么多,又为厂里奉献了全部青春,能不能让我也拍一部?
吴厂长知道这人才能一般,当场也给他跪下了。
说你这么多年都没拍了,也不差这一部,还是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吧。
两人对视了一会儿,这人才讪讪起身走人。
等《红高粱》在柏林勇夺金熊奖的重大利好传来,又斩获了金鸡、百花的最佳故事片,这些风言风语才算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