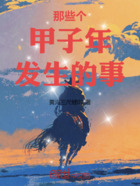
第514章 公元前117年之大汉王朝(二十五)
《史记》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巨著,
在历经千年的流传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文本的变迁和补窜。
这些变化使得今本《史记》中的某些篇章或段落已非司马迁原著,
而是后人根据当时的理解和需要所作的补充和修改。
这种补窜现象在古籍流传中并不罕见,
它反映了不同时代对同一文献的不同解读和需求。
例如,在《司马相如列传》中,
扬雄的评价“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显然带有后世的文学批评色彩,
不太可能出自司马迁之手。
《公孙弘传》中提到的“汉平帝元始中诏赐弘子孙爵语”,
则明显是后来的历史事件,不可能在司马迁的时代出现。
《贾谊传》中的“贾嘉最好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语”也显示出了补窜的痕迹,
因为这些内容超出了司马迁所处时代的知识范围。
对于《史记》中缺失篇章的补写,历史上有多种说法。
裴骃在《太史公自序》末注文中引用张晏的话,提到《史记》亡失的十篇中,
有四篇是由褚少孙补续的,包括《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和《日者列传》。
然而,张晏也指出这些补续的言辞鄙陋,与司马迁的原意不符。
张守节在《龟策列传·正义》中则认为褚少孙补了全部十篇,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持相同观点。
根据《汉书·艺文志》、《论衡·须颂篇》、《后汉书·班彪传》注以及《史通·古今正史篇》等文献,
西汉后期补续《史记》的作者多达十七家。
张大可认为,真正补续《史记》的只有褚少孙一人,
其他人的续写实际上是对西汉史的补充,
且大多单独流传,与褚少孙的补续附于《史记》之后的情况不同。
赵生群则根据相关资料,认为除了褚少孙之外,
冯商也是真正补续《史记》的人之一,
《汉书·艺文志》中对冯商所续的《太史公》保留了七篇,应是补亡之作;
删除的四篇,则应是续《史记》之文。
这些补窜和续写的情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史记》的原貌,
但也体现了《史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响力和价值。
每一代学者都在努力还原和理解司马迁的原著,
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和丰富着这部伟大的史书。
《史记》的流传和演变,不仅是文献学的研究对象,
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承和演变的一个缩影。
崔适在其著作《史记探源》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
他认为《史记》原本属于今文学,但由于刘歆的窜乱,导致书中掺杂了古文说。
刘歆是西汉末年的学者,曾参与古文经学的整理工作,崔适认为他伪造了《左传》,
因此《史记》中凡与《左传》内容相同的部分,都是刘歆所窜入的。
这一观点对后世的《史记》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崔适还提出了“麟止”理论,
即《史记》的记载应断限于汉武帝元狩元年,也就是“麟止”之时。
因此,他认为“麟止”之后的所有记载都是后来窜入的。
根据这一理论,崔适列举了29篇他认为是后人补写或妄人续写的篇章,
包括《文帝纪》、《武帝纪》、《年表》第五至第十、八书、《三王世家》等,
这些篇章在崔适看来,并非出自司马迁之手。
对于这些篇章的补写,崔适特别指出《年表》第五至第九为褚少孙所补,
而其余的则是其他人所续。
褚少孙是西汉时期的学者,被认为是《史记》补篇的主要作者之一。
朱东润在《史记考索》附《史记百三十篇伪窜考》一文中,
对“十篇亡佚”以及崔适提出的二十九篇补续和其他涉及的篇目共四十八篇进行了详细的辨析。
朱东润在文中既有肯定前人观点的地方,也有反驳前人观点的地方,
展现了他对《史记》文本真伪和窜入问题的深入思考和严谨态度。
这些讨论和研究,不仅体现了《史记》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重要地位,
也反映了学者们对于历史文献真实性的不懈追求。
尽管存在争议,但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史记》的成书过程、文本变迁以及历史价值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和资料。
《史记》的这些研究,至今仍是史学界和文献学界的重要课题。
泷川资言在其著作《史记会注考证·史记总论》中的“史记附益条”提到,
《史记》中涉及补窜的篇目共有三十四篇,
这些篇目涵盖了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等不同的体裁。
这些篇章中,有些被认为是褚少孙所补,有些则被认为是后来人补窜的。
这些补窜的篇目包括《秦始皇本纪》和《今上本纪》两篇本纪;
《三代世表》、《汉兴诸侯年表》等六篇表;
《礼书》、《乐书》等八篇书;
《陈涉世家》、《外戚世家》等七篇世家;
以及《贾生列传》、《郦商列传》等十三篇列传。
今人张大可对这些补窜篇目进行了详细的考释,
他认为除了上述三十四篇外,《孔子世家》、《韩信卢绾列传》、《匈奴列传》、《大宛列传》这四篇也属于司马迁之手的窜补篇目。
张大可将所有补窜篇目内容分为四类:
褚少孙等续史篇目内容、好事者补亡篇目内容、读史者增窜篇目内容、司马迁附记太初以后事篇目内容。
在这四类中,共有十六篇涉及太初以后的记事,
涉及二十二人,这些内容是司马迁对历史变迁“综其终始”的简略附记,总计1541字。
这些人物和事件主要集中在巫蛊案和李陵案两件大事上。
赵生群则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史记》的记事应该截止于太初,
太初以后所记载的事件应该是后人补窜的。
这种观点认为,太初以后的内容不属于司马迁的原著,
而是后来者根据当时的需要和理解添加进去的。
这些关于《史记》补窜篇目的讨论,
反映了学者们对《史记》文本真实性和完整性的重视。
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结论,
他们的工作为我们理解《史记》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深度。
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史记》的认识,
也展示了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史记》的成书过程,
以及它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经历的变迁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