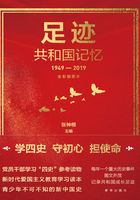
1954年 登上国际舞台
朝鲜战争结束后,亚洲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中国人民争取与维护世界和平的信心大大增加。毛泽东提出:“形势是很好的,应该派一些同志去做外交工作,做外交就是做建设工作。”党中央要求在外交方面开展积极的活动和斗争,为新中国刚刚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先后参加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和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开始了新中国登上国际舞台的成功实践。
第一次唱“正规戏”
1954年4月,在苏联的推动下,由美、苏、英、法、中及有关国家外长参加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性会议。会议讨论的两个问题都与中国密切相关,党中央非常重视,中国代表团作了系统认真的准备。临行前,周恩来向代表团成员做了仔细的叮嘱: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那是野台子戏。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

1954年,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出席了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图为日内瓦会议开幕时会场一角。第三排右起第三人为周恩来。(新华社发)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参加讨论朝鲜问题的国家,除了中、苏、美、英、法及朝鲜南北两方外,还有参加过朝鲜战争的澳、比、加等12国代表。从4月27日到6月15日,会议重点讨论朝鲜问题。在长达近2个月的时间里,由于美国的阻挠,会议陷入僵局。
6月15日,是讨论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气氛尤为紧张。面对美国等国想把在日内瓦会上继续讨论朝鲜问题的大门完全关死的风险,周恩来挺身而立,舌战群雄,他以特有的政治敏感和折冲樽俎的斗争艺术,敏锐地意识到有些国家希望达成一个“不能达成协议”的协议,以结束会议。周恩来在关键时刻提议:“日内瓦会议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问题的决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他还补充强调:“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
周恩来提出的“最低限度、最具和解性的建议”,获得很多国家代表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即便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代表依然声称“不准备在未向美国政府请示的情况下同意这个建议”。
虽然日内瓦会议上历时51天的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在美国的阻挠下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结束。但它让中国察觉到“美国在表面上很凶,但背后却很虚弱,”“朝鲜问题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问题已看得很清楚,再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小了”。
在日内瓦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抓住机遇,在英、法及苏、越等国代表之间进行了卓越的外交斡旋,最终促使会议达成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会场外,周恩来利用一切机会同各代表团和各方面人士接触,包括居住在瑞士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卓别林等。他还邀请许多国家的朋友观看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接触中,周恩来真诚、坦率、机智和潇洒的个人魅力,给人们特别是没有和新中国接触过、原来心存疑虑的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因此,有人称新中国的外交为“周恩来的外交”。
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

1954年7月18日,周恩来在日内瓦宴请居住在瑞士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卓别林(左二)及夫人。(新华社资料照片)
日内瓦会议基本达到了中国预定的目标,显示了刚刚登上国际舞台的新中国坚持正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形象,在解决国际争端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求同存异”促成共识
1954年4月,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倡议召开亚非会议,讨论亚非地区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12月底,五国总理再次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决定正式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于1955年4月的最后一周在印尼万隆举行亚非会议。
1955年4月18日,29个国家的340名代表齐聚万隆,会议隆重开幕。
万隆会议是由亚非国家发起和出席、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它反映了亚非人民反对殖民统治、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促进亚非各国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中国是亚非地区最大的国家,本着为“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物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的原则,应邀参加会议。
尽管中国代表团出师不顺,美蒋反动势力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但这种卑劣的行径并不能阻挡中国人民谋求和平与合作的脚步。在严峻的形势下,周恩来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坚定地说“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依然率团出席会议。
会议过程形势复杂、波折颇多。美国极力阻挠、破坏会议,挑拨亚非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而且与会国家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又互不相同,对重大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
在会议第一阶段,即各国代表发言阶段,就出现了一波反华风潮。开幕日下午,伊拉克代表发言称共产主义是独裁,是新殖民主义,要反对共产主义。一些国家附和,对中国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不信任,甚至攻击共产主义。19日,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等国代表纷纷指责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怀疑中国对邻国实行“颠覆”活动。一时大会气氛紧张,与会代表都关注会议的发展情况。
面对复杂局面,周恩来以他卓越的外交才干和出色的斗争艺术将会议从可能走上歧途的方向扭转。
19日上午,周恩来临时决定将原来的发言稿改为书面发言分发,并在下午的会议上作补充发言。据时任中国驻印尼使馆外交官的黄书海回忆:周总理第一句话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第二句话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的而不是来立异的”。简洁直白而又振聋发聩的开场白,吸引了与会代表的注意。
周恩来从容不迫地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他强调“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并且阐述亚非各国遭受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的共同基础,彼此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图为周恩来总理1955年4月19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作补充发言。这18分钟“求同存异”的补充发言征服了全场,树立了新中国真诚友好的形象。(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摄)
周恩来还回答和解释了亚非国家中不同的思想意识与社会制度问题,所谓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以及所谓中国支持颠覆活动问题。周恩来最后呼吁:“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的发言诚恳,尤其是“求同存异”的提法使与会者感到合理而且亲切,赢得了广泛赞许,改变了会议气氛。后来会议主席、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对周总理表示:“您的讲话太好了,将整个会议气氛扭转过来。”
针对会议讨论的殖民主义问题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法的问题,周恩来以坚定的原则性和高超的灵活性将问题一一化解。“周恩来利用了他个人的巨大魅力和外交机敏逐渐减弱了那些怀疑中国,或怀疑共产主义的领导人的敌对情绪。”4月24日,全体会议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亚非会议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又取得新的进展。
从日内瓦会议到万隆亚非会议,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并逐步走出“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