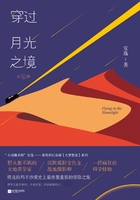
第12章 都怪花香太撩人
“没在沙漠里看过星星的人,不会知道夜色有多迷人。”
——程旷
这晚,基地外面如过节一般热闹。
只可惜森林易燃,连欢聚都只能选在远离基地的沙坳里。但这丝毫没有降低众人高涨的热情。
他们在渺无人烟、寸草不生的沙地上燃起篝火,宰了三头羊,架在火上烤得金黄流油,孜然与羊肉的香味,飘出十里。
七八十号人围坐在一起,唱歌、跳舞、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笑闹成一团。
据说,因为经费被冻结,这里曾经聚集的几百号人,已经走得只剩下眼前这些了
整整五十平方公里的基地,全靠这百十号人维护。
每个人都不得不身兼数职,平时基地里供应大家吃的菜地,也是人人都要抽空去打理的,连程旷也不例外。陆晋就跟着她去菜地里躬着腰割过葱、撒过种。
此刻,陆晋被裘胜灌了一大碗酒,浑身烧得火热。
夜晚的风,劲烈如虎扑,扑得篝火“噼噼啪啪”地响。火苗借了风势,蹿得老高,焰光照亮了半边天,照得围坐在它周围的人脸膛亮堂堂的,透着喜气。
火光映着大碗喝酒的程旷,映着丁克羞涩的小红脸,映着摇头晃脑的施一源,映着痞里痞气地挑着娄云斗嘴的裘胜,映着跛着脚载歌载舞的艾尔肯……
当这群人知道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评估师的时候,他要怎么面对他们呢?
这些原本陌生的人,又一次透过陆晋的眼睛,走进了他的心。
尽管他无数次告诫自己,要紧闭心门,才能客观,才不会受到伤害。
可是这些人,这些活生生、会哭会笑会转瞬就停止呼吸的人,总是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闯进他的心里,让他承受不该属于他的情感和痛苦。
陆晋忍不住轻蹙起眉头。
一回头,他却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坐在他身边的程旷已经没了踪影。
没有人知道,闹腾起来比十个人还大声的程旷,其实并不喜欢热闹。
越是热闹喧哗,结束后越是凄清空虚,灯灭火熄、人走茶凉后那漫长的孤独感,才最是折磨人。
从小,程旷就不喜欢燃过烟火后空荡荡的夜空,太寂寞了。
于是,她宁肯一开始就不参与这热闹里,这样就不会有抽身时的不舍。
程旷是在酒意上头的刹那离开的。
她独自走了很长一段路,踢着脚下的沙,不知不觉顺着渐浓的蜜香,走到沙枣树林里。
她轻车熟路地找了一棵最粗壮的树,踩着突出的树节,三两下攀上去,摸到那根躺惯了的、横伸而出的树杈,斜靠了上去。
她闭上眼,放任自己浸淫在蜜糖的香味里,想象着这些花朵全变成了沙枣,红艳艳地结成串,果实累累压弯了枝条,摘一个吃在嘴里,沙沙粉粉的甜弥漫开来。
难得歇口气,她要吸一肚子的花香,晚上睡觉时,就能做个香甜的梦。
连日来提心吊胆地编织谎言,赶制地下水纹图,对陆晋严防死守,和众人讨论打开温室后的一系列后续工作,令她疲惫不堪。
自己大概是老了,经不住折腾了。
程旷下意识地捏了捏腰部,紧绷绷的,用手指一捻,只能拎起一层菲薄的皮肤,一点多余的脂肪也没有。
还能再折腾好几年吧。
她放心了,在醉人的花香里,恍惚了心神。
没了程旷的严防死守,陆晋竟然有点不习惯。
音乐被扩音器放得震天响,几十号人划拳喝酒、唱歌嬉闹,吵嚷出巨大声浪,一层一层拍击着他的脑袋。
向着火的面颊被烤得发烫,可是后背被夜风一撩,又透心地凉。
裘胜的酒烈如刀,割得他头痛。
陆晋起身,借口如厕,稍稍走开一些,想要避开令他心烦意乱的人群,不知不觉,便走得有些远了。
炭火的味道、孜然的辛辣、羊肉的香味,混着酒气被汹涌的夜风一吹,也淡了。
隐隐约约,有蜜糖的香味被远处的风送到鼻端。
他突然想要安静一会儿。
陆晋加快脚步。他要离这些人远一些,再远一些。
他不断提醒自己,得和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才不会受到伤害。
无数次血的教训,令他明白,离任务目标太近,只会徒惹麻烦。
他再不要用别人的痛苦,来折磨自己了。
那花香好像会引路,醉酒的人不知不觉便被它诱惑,顺着它的指引,陆晋踉跄着就步入了蜜香深处。
直到那黑漆漆只有淡薄星辉勾出一点银色轮廓的沙枣林将他团团围住,他才惊觉自己到了何处。
他突然想起幼年时学过的一首词: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他这算是误入枣花深处吧。可惜,什么也没惊到。
他正自嘲,突然踩到一根树枝,寂静中发出“咔嚓”一声脆响,头顶大树应声剧烈一晃——
有重物忽然从树上滚落下来,直直向他砸来。
饶是有了三分醉意,陆晋仍然条件反射地向旁边疾退数步,闪身掩到树后,蹲身抱头。
“砰咚”——那重物几乎是在他闪开的瞬间,重重落在地上。
睡得昏天黑地的程旷,被那声脆响一惊,下意识侧身。
她浑然忘记自己正躺在树上,待她清醒过来时,身体已经悬空,连惊叫都来不及,便重跌在了地上,脸朝下,双手摊开,摔了个结结实实。
陆晋闻声,抬起头望过去。
借着稀薄的星光和半钩月华,他隐约看见地上匍匐了个人,正嘶嘶啊啊地惨号不已。
那人像感觉到了他的注视,猛地抬起头,一只眼如电光般直直地射向他。陆晋被这一眼吓得差点跌坐在地上。
竟然是程旷!
程旷趴在地上,抬着头,陆晋蹲在她面前,略垂着头。
三目相对,彼此眼里的醉意,清晰横陈在眸中,两人都是一愣。
“哈哈……”陆晋忍不住笑出声。
程旷从沙地上撑起上身,狠狠地瞪了陆晋一眼,捂着撞得闷痛的胸口,“呸呸呸”粗鲁地吐着啃了满嘴的沙,也闷声笑了起来。
“你怎么……”陆晋指了指树,又指了指地。
程旷用露在外面的一只眼睛,翻了个白眼:“扰人清梦的人,没资格提问。”
“天为被,树为床,你真会选地方睡。”陆晋拍掌叹服。
程旷晃了晃头。摔了一下,酒精好像在她体内被搅匀了,脑袋一阵发晕。
她从地上爬起来,花香馥郁,她有点舍不得离开,干脆攀住树枝,一脚蹬在树身上,一个挺腰蹿了上去,继续在刚才的树杈上躺下来。
“一起睡?”她向陆晋招了招手,故意说得暧昧。
陆晋早已习惯她的不正经,当下便也不客气地打量了四周一圈,寻了程旷对面的一棵树攀上去,找了根粗壮的树枝,坐了上去。
一串沙枣花正好垂在他脸庞边,黑夜中看不清花蕊,却能闻到那连皮肤都会被浸软的香味,正源源不断地散发而出。
原来花香,一定要用夜色做衬托,才最诱惑。
密丛丛的沙枣树枝叶搭起的帐篷里,一个斜坐、一个半躺,两人一时竟找不到话说。
远处传来缥缈的歌声和哄笑,越发显得林中寂静幽深,那汹涌的花香,一波一浪,连绵不绝,竟好似有了独立的生命体,在晚春静谧的空气里,恣意发酵、伺机而动,几乎要把人心里藏得最深的情绪都勾出来。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两人异口同声地打破沉默,又忍不住同时笑了起来,笑得两棵大树簌簌晃动,真正是花枝乱颤。
程旷当下便举目向对面望去。
霜冷的月色从叶缝里流下,浮起一层银白的幽光,陆晋的脸并不能看真切,但他那双心事重重的眼睛,带着点寂寥,正沉沉看向她。程旷的心猛地像被头小兽从暗处撞了一下,险些跳出胸口。
她忍不住按了一下胸膛,啐了自己一口:真是春天到了。
“我不喜欢人多。”她清了下嗓子,朗声回应,一派月白风清,坦荡无畏的做派。
陆晋点了点头,有点意外。她一向是最闹腾的那个。
“温室拆了,接下来就要等雨了吧?应该可以休息一阵了。”陆晋在花枝后面,打量了一下对面的程旷,借着一点月光的反射,那唯一的一只眼在暗处亮得十分惹眼。暗夜里的篝火也是这样生猛、霸道、熊熊不息,所有靠近她的人,都会被这旺盛的生命力灼伤。
“休息?”程旷“噗”地笑出声,嘴里浓重的酒气在干冽的空气里一渡,涌到陆晋跟前,那沙枣花的甜香里,便带了几分醉意。
“接下来才是关键!”程旷醉憨憨的语调里添了劲道,像松弛的肌肉在承受外力时,不由自主地绷成硬块,“我们铆足劲儿就等着今天。眼下我们五十平方公里的植物,全赖消耗地下水存活。如果不能改变气候,基地就是一座废物。”
“如果不下雨,计划终止,你准备怎么办?”陆晋有点担心,他很清楚程旷是个一根筋的女人。
“这问题,我还真没考虑过。”程旷露齿一笑,白森森的牙在黑夜里有点狰狞。
“哦?”陆晋的提问越发言简意赅。
“也许,我可以——去迪拜或者沙特!很早之前,就有人给过我Offer,薪水是现在的十倍。毕竟沙漠国家,水是最精贵的。”
“那你怎么不去?”陆晋问。
程旷大笑道:“我喜欢更具挑战性的工作。你如果从外太空看地球,会发现黄褐色的沙漠占据了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一,是地球难以愈合的伤疤,这疤痕正在不断壮大,向外扩张,与人类争抢土地。只有在这里工作,我才有机会治愈这些疤痕。当沙漠全部变成森林,黄沙进化成肥沃的土壤,那些岌岌可危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我猜,人们一定会给我塑一座像的。”
随着程旷朗笑低语,陆晋好像真的看见一片葳蕤的绿色森林中,耸立起一座英俊挺拔的塑像——还戴着一只黑色的、匪气十足的眼罩。
“钱对你来说从来不是问题,对吗?”陆晋想到自己目前的生活窘境,如果不是接到这单任务,可能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
“我要钱来做什么?”程旷又恢复了醉醺醺的痞子语调,“我一生都准备待在鸟不拉屎的沙漠里,有钱也花不出去。”
“你就没想过,找个男人结婚生孩子过日子?”陆晋好奇地问道。
“我为什么要结婚?”程旷大言不惭道,“多数女人结婚,是妄想从男人身上获得安全感和力量。这两样我都不缺。”
“可是孤单一人,不寂寞吗?”
“习惯了!”程旷想了想,认真道,“这世上,谁又不寂寞呢?同床异梦的冤家还少吗?一个人内心的平静和强大,比找个伴侣更重要。倘若一个人也能活得精彩自由,又何必执着于结婚生子?我的事业就是我最好的伴侣。”
“你觉得沙漠里的生活,算精彩自由吗?”陆晋喝多了酒,问题有点多。他觉得程旷除了工作,并没有真正的生活。
“当然精彩!没在沙漠里看过星星的人,不会知道夜色有多迷人。”程旷指了指头顶。
夜色深蓝,繁星密集如鱼群,一点云翳也看不到。对着这样无边无际的夜空,看久了,竟然觉得头晕,好像一头扎进了深海之中,触目都是璀璨的宝光。
“何况——沙漠里开车没有红灯。”程旷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还不需要驾照。”
陆晋沉默了,就算酒精一阵阵折磨着他的头,刺激着他的舌头想要畅所欲言,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女人奇异的想法。
反正,她就是准备嫁给沙漠了。
听说女人都想改造自己的伴侣,看来她也不例外。
“如果下雨了呢?”陆晋又问。
“下雨了,就去集团申请接下来的研究经费!我和岳老一直在绘制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地下水纹图,会另外挑选十个符合条件的地方建新基地。随着基地的不断增多,雨水就会越来越充沛,地下水资源也会丰富起来,直到整个沙漠被绿色覆盖。”程旷喜滋滋地说道,好像她的眼前已经是绿意盎然的葳蕤森林了。
“真有那一天,也是一百年以后的事了吧?”陆晋忍不住泼她冷水。
“那有什么关系?”程旷说,“做人目光要长远。”
“可是再长远,你也看不到了啊。”
“能看多少算多少!”程旷很坦然,“梦想最美妙的阶段,不是实现之际,而是不断接近它的时候。”
漆黑的沙枣林又陷入一片寂静。
这种静和以往不同。程旷想,以前的静里,只能听见大自然悄无声息的吐纳,植物在沉默地舒展、生长。
而眼下——眼下的静里,还多了一个男人的呼吸。
轻缓、均匀、绵长而有力,和女人清浅的呼吸非常不同。这样的呼吸,在这样的星光下,难免令人想入非非。
程旷耳边又响起娄云的话:“露水姻缘,也好过久旷而干。”
饶是程旷一向脸皮厚,黑暗中,她的手心也濡濡地出了一潮汗。难道真是旷久了?
一会儿,裘胜的话又跳进她的脑袋里,嗡嗡地吵起来:“沙漠里太干,女人在这里待久了,不能阴阳调和,跟干尸似的,一点都不水灵。”
程旷又觉得心里燥热起来,胸口胀鼓鼓的,好像有个声音一直充斥其间,想要对月“嗷嗷”叫上几声。她暗道不好,莫非真是女人三十如狼?
不不不!这只是喝多了酒,口干舌燥而已。
这边程旷在春日浓稠的气息里,心绪烦乱。
另一边的陆晋,则内心一派安宁。
他一点也不觉得沙漠生活枯燥乏味。尽管这里没有手机,不能上网,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成日只能跟在程旷身后看她忙前忙后,可是,这里真安静啊。没有炮火,没有喧嚣,没有蝇营狗苟的人生,也没有碌碌无为的庸常和钩心斗角、明争暗斗。每个人心里都揣着一团火,眼里都亮着希望。他们都在为着一个伟大而遥不可及的目标在奋斗。
就像他之前所做的一切,十年枪林弹雨,游走在死亡的边缘,为的也不过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换了别人,一定会说他天真。可是此刻,他想,如果是程旷,或者基地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说他天真。
他没想到,离开了人满为患的大都市,反而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里找到了知己。
两人沉默着,在这春风沉醉的沙漠之夜,在沙枣花的蜜香中,在不知名的昆虫窸窸窣窣的动静里……
直到夜风越来越劲,连天上的星星都泛起了冷意,程旷摸了摸被风吹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的手臂,率先从树下跳了下去。
黑暗中她仰起脸,对陆晋说:“回去吧。”
陆晋二话不说,也跟着一跃而下。
程旷熟门熟路,在前头带路。也许是喝了酒,也许是花香太过撩人,她总觉得身后陆晋的双眼自带温度,盯得她背心发烫。
她不由得加快脚步,然而风一吹,酒劲越发上头,一步一步踏出去,都好像踩在虚空中,只有鞋子与沙子,摩擦出“沙沙”的声响,越发显得空旷,身后男人的呼吸声也越发清晰。
她心猿意马地走着,一不留神,便被不知什么灌木凸出地面的树根绊了一下,整个人当即刹不住车地向前一扑——
就在这刹那,一只结实有力的手臂从后面一把拉住了她,拉力又凶又狠,一下就将她扑出去的那股势头止住了。
程旷有点尴尬地回身后看,只看见男人一双微微下垂的眼,她不动声色地凝视着他,那目光幽深沉着,带着几分不可明说的神秘,混着撩人的花香,直往她心里钻去。
夜风那么凉,吹得人心里发慌,而他握着她手腕的掌心,是那么滚烫,像突突的温泉,涌出无边的热流。
她一向行动快过思维,几乎是下意识地手腕一翻,一把握住了陆晋的手,掌心相向,十指相扣。
她的手冰凉,陆晋的手火热,像冰块与烈酒撞击在一起,在心里发出“叮”的一声清响。
陆晋愣了一下,却也没有挣脱,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程旷也定定地看着他那夜海一般的眼睛,想要看清里面是否藏着湍急的暗流,可是,这双眼太黑、太沉、太安静,再繁复的情绪都被遮掩得密密实实。
她的心,像被天外飞来的一颗流星给撞击了,撞出一个缺口,堆积了三十年的柔情全部不管不顾地往外涌。
她觉得心慌意乱。
但她是谁?
她是这沙漠里,野风一样不羁的程旷。
她必须控制住场面。
于是,程旷突然冲着陆晋笑了一下。
夜色里,那笑容如同篝火里飞溅出来的火星,热力逼人。
她有一口极白的牙齿,每次大笑都会露出整整齐齐的八颗牙,好像全天下所有的阴霾都会在这八颗大牙明明晃晃的快乐里被驱散。
她用力晃了晃两个人交握在一起的手,又低头闷笑了一会儿,然后仰起脸,冲他得意地小声道:“别怪我,要怪就怪这花香太撩人。”
陆晋的眼里便带出几分淡薄如水的笑意。
他用力回握了一下掌心处那只纤薄冰凉的手,她掌心的薄茧与他掌心的薄茧厮磨,带出微微酥麻的电流。
好像得到鼓励似的,程旷就这样一直牵着陆晋的手,大步朝林子外走去。
一边走,她还一边大弧度地晃动着两人交握的手。
陆晋心里便生出一种怪异的感觉——幼儿园小朋友一起手牵手过马路,也是这样的。
你拖着我的手我拖着你的手,前晃一下,后摇一下。
他突然觉得,刚才在心里生出的那点旖旎情愫,是那么的不合时宜。
眼前这位号称三十岁的女匪首,分明有颗赤子之心。
呃!或者说是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