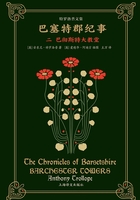
第6章 战争
“我的天!”会吏长一脚刚踏上砂砾小路,便这么喊起来。他一只手摘下帽子,一只手多少有点儿激动地抹了抹这时已经灰白的头发。热气从摘下的海狸皮帽子里冒出来,好像是一阵怒气,他的怒火的安全阀打开了,放出来一种清晰可见的蒸气,防止了实际的爆炸和可能的中风。“我的天!”——会吏长抬眼望着大教堂钟楼上那个灰色的尖顶,默默无语地向那个还生气勃勃的“见证人”发出了呼吁,这个“见证人”曾经从那儿俯视着巴彻斯特那么许多位主教的所作所为。
“我大概决不会喜欢这个斯洛普先生。”哈定先生说。
“喜欢他!”会吏长吼起来,他站定了一会儿,好使自己的嗓音更为有力。“喜欢他!”教堂区里所有的乌鸦都呱呱叫着表示同意。钟楼上的老钟在发出和谐的铿锵声报时的时候,也应和了这句话。燕子从窝里飞出来,默默地表达出了类似的意见。喜欢斯洛普先生!嗐,不啊,巴彻斯特任何土生土长的有生命的东西,全不大可能会喜欢斯洛普先生!
“也不会喜欢普劳迪夫人。”哈定先生说。
会吏长这一下完全忘乎所以。我可不来学他的样,也不把他表达他对提到的那位夫人的情绪使用的词句记录下来,使读者们大吃一惊。乌鸦和最后慢悠悠消逝的钟声全不那么顾虑重重,它们用相应的回声一遍又一遍重复着那个很不合式的喊叫。会吏长又把帽子掀了掀,又放出了一阵有益于健康的蒸气。
沉默了一会儿。此时领唱人极力想领会这一事实:即巴彻斯特一位主教的妻子,在大教堂区里竟然给它的会吏长亲口唤作这样一个名称,可是这一点他却做不到。
“主教似乎倒是个很文静的人。”哈定先生暗自承认做不到那一点以后,便这么说。
“白痴!”博士喊着说,他当时只能这样痉挛性地喊上一声。
“唔,他似乎不很精明,”哈定先生说,“可是他一向却有为人精明的名声。我想他是很慎重,不想随随便便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
巴彻斯特的新主教在格伦雷博士的眼里,已经是那么可鄙的一个家伙,他简直不屑自贬身份去讨论他的性格了。他是一个由其他人摆布的木偶,——仅仅是一个蜡人,穿了一件长坎肩,戴了一顶铲形帽[83],任凭人家推到一个宝座上或是什么别的地方,随便人家用铁丝拖来牵去。格伦雷博士不乐意大失身份,去谈论普劳迪博士,不过他瞧出来,他不得不谈到他家里的其他成员,那两个主教助理。他们可以说是用只盒子把主教带到这儿来,正准备按照自己的意愿操纵铁丝。这件事本身由会吏长看来,就是极其令人恼火的。要是他能够不理睬那个家庭牧师,和主教对阵,那么在这样一场较量中,至少不会有什么大失身份的地方。让女王乐意派谁就派谁来做巴彻斯特的主教,人也好,大猿也好,他一旦当上主教,就是一个体面的对手,只要他本人肯战斗的话。可是当另外一个人像斯洛普先生那样,给推上前来作为对手,那么像格伦雷博士这样一个人又该怎么办呢?
如果他,咱们的会吏长,拒绝作战,那么斯洛普先生就会扬扬得意地走过战场,把巴彻斯特主教区踩在他的脚下了。
另一方面,如果会吏长把新的傀儡主教推到他面前来作为对手的那人当作他的对手,那么他就不得不谈到斯洛普先生,写到斯洛普先生,并且在所有的事务上和斯洛普先生商谈,把他看作一个多少和自己地位相等的人。他就不得不会见斯洛普先生,不得不——呸!这个想头就叫他厌恶。他实在没法让自己去和斯洛普先生打交道。
“他是我瞧见过的最最像野兽的人啦。”会吏长说。
“谁——主教吗?”另一个人很单纯地问。
“主教!不——我可不是在说主教。那样一个家伙怎么会成为牧师的!——我知道他们现在把圣职随随便便就授给人,不过他这十年都在教会里工作。十年以前,他们一向总稍许谨慎点儿。”
“啊,你是说斯洛普先生。”
“您瞧见过有哪个畜生比他更不像人样吗?”格伦雷博士问。
“我可没法说我会喜欢他。”
“喜欢他!”博士又嚷起来,那些深表赞同的乌鸦又呱呱地应和了一番。“您当然不喜欢他啦。这并不是个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可是咱们拿他怎么办呢?”
“拿他怎么办?”哈定先生问。
“是呀——咱们拿他怎么办呢?我们该怎样对待他?他来啦,他可要待下去。他一脚踏进了那个公馆以后,在人家把他赶出去以前,是不会再走出来的。咱们该怎样来除掉他呢?”
“我认为他并不能给咱们带来多大害处。”
“没有害处!——哼,一个月不到,您的看法大概就会不同啦。要是他现在想法给派到养老院去,那么您会怎么说呢?那是害处吗?”
哈定先生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他认为新主教不会把斯洛普先生派到养老院去。
“如果他不把他派到那儿,他就会把他派到一个别的地方去,他到那儿也同样够瞧的。我告诉您,那个人实际上是要来做巴彻斯特主教的。”格伦雷博士说着,又把帽子掀了掀,深思地、伤心地用一只手在头上抹了抹。
“不懂规矩的恶棍!”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下去,“竟然敢来盘问我主教区里的主日学校,还有星期日的旅行。我一生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在冒失无礼方面像他那样的人。咳,他准以为咱们是两个谋求当牧师的人哩!”
“我认为普劳迪夫人实在是两个人中最恶劣的一个。”哈定先生说。
“一个女人要是傲慢无礼,你只要容忍一下,往后躲避开她,那就成啦,但是我可不想容忍斯洛普先生。‘安息日旅行!’”博士想要模仿他如此嫌恶的那个人的那种特别的、拖声慢气的语调。“‘安息日旅行!’要把英国国教毁掉的就是这路人,他们会使牧师这种职业很不体面的。我们应该担心的,并不是不信奉国教的人或是罗马教徒,而是这帮说得好听、没有教养、正千方百计想混到咱们中来的伪君子。这帮人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标准的宗教思想或教义概念,可是却拾起一个很得人心的口号,像这家伙利用‘安息日旅行’这样。”
格伦雷博士没有把那句问话大声再说上一遍,不过他却一直这么暗自问自己,“他们该拿斯洛普先生怎么办?他该怎样当着全世界公开表明,他完全不赞成这样一个人,他厌恶这样一个人?”
顶到这时候为止,巴彻斯特一直逃脱了任何极端严厉的教条的污染。城内和附近一带的牧师虽然很想促进高教派的原则、特权和特殊利益,却始终没有对那些未免不甚严格地唤着普西主义[84]的习惯倾向承担义务。他们穿着黑法衣讲道[85],像他们的父亲在他们之前所做的那样。他们还穿着普通的黑布背心,他们的圣坛上没有点亮的或不点亮的蜡烛,他们私下没有行跪拜礼,而且他们满足于谨守着过去一百年中流行的那种礼仪。礼拜式在教区教堂里总是庄重严肃地朗读出来,唱歌则只限于大教堂,而吟诵的学问还不为人所知。有一个直接从牛津来当普勒姆斯特德副牧师的青年人,经过两三个星期日之后,稍稍做了一次尝试,使会众中的穷人感到大惑不解。格伦雷博士那一次并不在场,但是格伦雷太太对这问题有她自己的主张,她在礼拜式之后立刻表示,希望这个年轻的先生没有生病,并且提议把各种据信是治疗咽喉炎的调味品送去给他。在那以后,普勒姆斯特德—埃皮斯柯派就不再有人吟诵了。
可是这时候,会吏长开始筹划着某种坚决反对的有力措施。普劳迪博士和他那一伙是国教牧师中卑劣到无可卑劣的一派,因此他,格伦雷博士,就应该是最最高尚的一派。普劳迪博士要废除各种仪式与礼节,因此格伦雷博士突然感到有必要增加它们。普劳迪博士会同意夺走教会的全部集体权力与统治,因此格伦雷博士就坚决支持教士会议享有的全部权力[86],并且坚决支持恢复它的全部古老的特权。
不错,他自己在礼拜式上不能吟诵,但是他可以找到许多举止高雅的副牧师来和他合作,而他们对于这么做的秘诀都受过很好的训练。他不会乐意更改自己服装的式样,但是他可以使巴彻斯特有许多穿着胸部最短的绸背心和最长的法衣的年轻牧师[87]。他当然不准备在自己身上画十字,或者提倡实在论[88],但是不这么做,也可以有许多不同的仪式。他采用这些仪式,就可以明白表示他对普劳迪博士和斯洛普先生那种人所起的反感。
当他和哈定先生在大教堂区来回踱步时,所有这些想头掠过了他的脑海。他心里只想到战争,两败俱伤的战争。他觉得,就巴彻斯特城而言,他自己和斯洛普先生两人中必须有一个给消灭掉。而除非到了不剩下一英寸土地容他立足,要不然他是不打算退让的。他仍然自以为,他可以使斯洛普先生在巴彻斯特简直待不下去。如果他有力量这么做,他决不会意志软弱,不来做到这一点的。
“苏珊大概非得上公馆去拜访一趟了。”哈定先生说。
“是的,她是得上那儿去拜访一趟,不过只去一趟,就只一趟。我想‘那些马儿’不会觉得很快就到普勒姆斯特德来是挺合适的。等这趟去过以后,这件事也许就算了结啦。”
“我想爱莉娜总用不着去拜访,爱莉娜和普劳迪夫人大概决不会相处得很好的。”
“压根儿没有必要。”会吏长回答,同时还想到,他妻子有必要遵守的礼节,约翰·波尔德的寡妇也许根本就没有必要遵守。“要是她不乐意,那么她没有一丁点儿理由应该去。拿我个人来说,我认为随便哪个正派的年轻女人都不该碰上这种讨厌的事,去跟那个家伙同待在一间房里。”
这样,这两个教士分手了,哈定先生到他小女儿的家里去,会吏长则坐上了他的四轮马车。
主教公馆里新来的居民们对来访的客人表示出的意见,并不比来访的客人对他们表示出的好多少。虽然他们没有像格伦雷博士使用那么激烈的语言,他们私下却起了同样的反感,他们也和格伦雷博士一样十分清楚,有一场恶仗要打,而且只要“格伦雷主义”在巴彻斯特占着优势,“普劳迪主义”就简直没有容身之地。
说真的,斯洛普先生胸中是不是已经有一套比会吏长更完善的战略,一种更明确的敌对行动方针,这是很可怀疑的。格伦雷博士准备进行战斗,因为他发觉自己憎恶这个人。斯洛普先生事先就决定要恨这个人,因为他预见到必需和他作战。在他进入巴彻斯特以前,第一次察看carte du pays[89]时,他曾经想到要安抚一下会吏长,要哄骗他,奉承他,使他顺从,要凭奸诈而不是凭勇气去占据上风。然而,他稍许打听一下后便深信,他的全部奸诈都不会把格伦雷博士这样一个人争取过来,使他同意斯洛普先生将要采用的那种行动方法。他于是决计转而依靠自己的勇气。他立即看出来,公然跟格伦雷博士的全体追随者作战,对于他的地位是必不可少的。他故意策划了招惹他们生气的一些最有效的方法。
在到达巴彻斯特后不久,主教便通知教长说,经当时的驻堂牧师允许,他的家庭牧师将于下星期日在大教堂里布道。驻堂牧师恰巧是可敬的牧师维舍·斯坦霍普博士,他那时候在科摩湖[90]湖滨,正忙着为他享有盛名的那批珍藏的蝴蝶标本再增添上一些。或者不如说,要不是因为蝴蝶和夏季的其他种种事情,他原来是会住在教堂里的。代替他讲道的圣诗班助理,压根儿不反对由斯洛普先生来替他把该办的事办了。
斯洛普先生于是讲了道。要是一个讲道人感到有人听讲便很满意,那么斯洛普先生应当是心满意足的了。我有理由认为他是心满意足的,而且他离开讲道台时,深信自己做了走上讲道台想要做的事情。
这一回,新主教第一次在他的宝座上就座。安排了崭新的猩红色坐垫和幔子,还有崭新的金丝滚边和崭新的流苏。古老、雕花的橡木宝座,以及无数奇特的尖顶,向上一直伸到距离唱诗班座位的屋顶一半的地方,它们全给擦洗、掸拂过了,所以显得十分漂亮。啊,在早年那些快乐的日子里,我何等频繁地坐在那儿,在圣坛前面那些低低的长凳上,默想着我可以怎样小心翼翼地穿过那些木头塔楼,安安稳稳地一直爬到最高的尖顶上,这样来把一次单调沉闷的讲道消磨过去!
巴彻斯特的人全去听斯洛普先生讲道,不是为了听讲道,就是为了去瞻仰一下新主教的丰采。城里戴最漂亮的无边女帽的妇女全都到场,所有戴亮堂堂的牧师帽子的人也全到场。牧师席上坐满了人,因为尽管有些牧师或许待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他们的位子全由当天拥进巴彻斯特来的教友们坐满了。教长也在那儿,他是一个迟钝的老头儿,说真的,这时候年纪已经太大,不能常常来出席了。会吏长也到了场。而大教堂司铎[91]、司库、圣诗班领唱人、种种驻堂牧师和低级驻堂牧师,以及圣诗班的所有世俗成员,全都在那儿。他们准备用适当的乐曲与和谐的、表示欢迎的圣歌来歌颂新主教就职。
礼拜式的确举行得很出色。巴彻斯特素来是这样,因为唱诗班受的音乐教育非常好,嗓音全是经过仔细挑选的。赞美诗全唱得很动听,《谢恩赞美歌》唱得美极了。做连祷[92]的方式是今天在巴彻斯特还可以听到的那种,不过要是我的鉴赏力不错的话,是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听到的。巴彻斯特大教堂里的连祷,早就是哈定先生以他的技巧与嗓音全力从事的特殊工作了。听众拥挤,一般总能促成出色的表演。尽管哈定先生并不知道自己这方面作了任何特别的努力,但是他那天大概相当超出了平日的标准。其他的人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应当胜过他的教友们,这是很自然的。这样,礼拜式进行下去,最后斯洛普先生登上了讲道台。
他从圣保罗对提摩泰讲的戒律里选了一节作为讲题,讲到一个精神指路人必不可少的操守。事情立刻变得很清楚,巴彻斯特的善心的教士们要听上一次教训了。
“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93]这就是他的讲题。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地方讲这样一个题目,这样一位讲道人是会得到这样一批听众谛听的。大伙儿屏息静听,都感到十分惊讶。在斯洛普先生开始讲道前,不论巴彻斯特人对他抱有什么见解,在他讲道结束后,他的听众中没有一个人会把他错当成一个傻瓜或是一个胆小鬼了。
在一部小说里,我如果很拙劣地来叙述一篇讲道文,或者甚至重复讲道文的语言,那将是不合式的。在我尽力描绘出我笔下人物的个性时,一定程度上被迫讲到一些神圣的事物。然而我相信,决不会有人认为我是嘲笑讲道台,虽然有些人可能猜想,我没有意识到,牧师所应受到的那份尊敬。我可能怀疑教师绝无过错论[94],不过我希望我不会因此就被人指控怀疑他们教导的内容。
斯洛普先生在开始讲道时,显露了不少的机智,他用模棱两可的态度暗示,自己虽然卑微,站在那儿却是作为坐在他对面的那位赫赫有名的神学家[95]的喉舌。他说完这么几句开场白以后,举出了一条很正确的行为定义,这种行为是那位大教士[96]乐于见到当时归他管辖的牧师们奉行的。我们现在只需要说,他特别坚持的几点,正是主教区的牧师们最厌恶,和他们的习惯与见解最抵触的。高教派教士现在被人恶意中伤,称作不合潮流的教派,所有他们一向最重视的那些特殊的习惯与礼遇,全遭到了嘲笑、辱骂和谴责。而巴彻斯特主教区的教士们则全属于这个不合潮流的教派。
他根据自己的见解这样说明了一个牧师作为一个“无愧的工人”,应当如何“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以后,接着便解释应当如何去分解真理的道。这儿,他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种相当狭隘的看法,从古代历史中去引证他的论点。他的目的是,表达出他对所有过分讲究礼节的仪式所感到的厌恶,贬低任何可能不是被理智而是被语言的声音激起的宗教情绪,事实上就是侮辱大教堂的种种习惯做法。如果圣保罗讲到正确地读出真理这个词,而不是正确地分解这个词,那么他讲道文的这一部分就会更为中肯。不过讲道人的直接目的是宣讲斯洛普先生的学说,而不是圣保罗的学说,因此他相当巧妙地使引文具有需要的那种牵强附会的意思。
他在大教堂的讲道台上讲道,不能明确地说,大教堂的礼拜式中应当取消唱歌。他要是提出这样一个主张,就会做得太过火,使自己显得很荒谬,使听众感到很好笑。但是他可以用严厉的斥责暗暗提到教区教堂里吟诵的习惯,而他也就这么做了,虽然这种习惯在主教区里几乎是不为人知的。从那上面,他回过来,断言音乐在他们刚听到的典雅的礼拜式中比重过大,掩盖了礼拜式的含意。他说他知道我们祖先的习惯做法是不能在得到通知后立刻便放弃掉。老年人的情绪会受到损害。体面人的思想将大为震惊。他深知有许多人思考能力不够,受的教育也不够,无法领会,也无法知道,当表面的仪式比内心的情感更为重要时才生效的礼拜式,在内心的信念最为重要的时候,在牧师嘴里所讲的每一个词都易于理解地注入听讲人心上的时候,就会变得几乎是粗野的了。以前,群众的宗教是想象力方面的事。现在,在最近这些日子里,一个基督徒对自己的信仰应该有其理由——应该不光是相信而且要体会——不光是倾听而且要理解,这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了。我们早祷的词句按朴实、清晰的仪式读出来的时候,多么优美,多么恰当,多么浅显易懂啊!可是当那些词句以浮华媚人的音调唱出来时,它们的含意有多少是丧失了!等等,等等。
这是一篇将要当着会吏长格伦雷先生、圣诗班领唱人哈定先生和其余的人,当着教长和聚集在他们自己大教堂里的牧师会的全体成员,当着那些一年老似一年、做着他们特殊的礼拜式、深信这种仪式对种种预期的目的极为有益的人宣讲的讲道文!这还是由这样一个人讲的,一个parvenu[97]教士,一个并没有正式牧师身份的人,一个家庭牧师,一个闯到他们当中来的不速之客,像格伦雷博士说的那样,一个从玛丽勒博恩[98]的街沟里给耙出来的家伙!他们不得不坐着听完他的讲道!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连格伦雷博士也不例外,能够捂起耳朵,或者在做礼拜的时刻离开教堂。他们全有义务洗耳恭听,而且也没有任何力量立即进行答复。
也许,在文明、自由的国家里,人类眼下所受的苦难,没有比被迫听人讲道更难受的了。在这些领域里,除了一个讲道的教士,没有人有力量强迫听众默不作声地坐着,受尽折磨。除了一个讲道的教士,没有人能够任意讲上一些陈词滥调和奇谈新说,而又凭借无可争辩的特权,受到同样必恭必敬的聆听,仿佛他嘴里说出来的是热情奔放、雄辩有力的,或是条理分明、令人信服的语言。要是有位法学或医学教授站到一个讲堂上,在那儿滔滔不绝地说出一些无用的空话和枯燥乏味的词句,那么他就会对着空凳子讲学。要是一个律师试图讲话而又没有讲好,那么他往后就不会多讲。一位法官的指控除了陪审团、犯人和看守以外,没有人是非听不可的。议会议员的发言可以用咳嗽去阻挠,或者宣布法定人数不足而休会。市政议员们的发言可以遭到禁止。可是没有人能摆脱传道的牧师。他是时代的厌物,是我们这些辛巴德[99]无法摆脱的老头儿,是打搅我们星期日休息的噩梦,是使我们的宗教过于沉闷,并使上帝的礼拜式令人厌恶的梦魔。我们并不是被迫走进教堂的!不是,而且我们希望的还不只是这样。我们希望不要被迫离去。我们希望,不啊,我们坚决想要享受教堂仪式给我们带来的安慰,而且我们还希望我们可以这么做而不感到相当单调,因为那是通常的人性所不能忍耐的。我们还希望我们可以在离开教堂时,没有那种急切渴望逃走的感觉,这是平淡的讲道文通常的后果。
一位年轻的牧师多么心安理得地从曲解的引文中推断出错误的结论来,然后威胁我们说,如果我们疏忽了,没有遵守他给我们下的禁令,我们就要受到地狱[100]中的种种惩罚!不错,我的过于自信的年轻朋友,我的确相信那些在你嘴里说得那么普通的宗教仪式。我的确相信你掌握在手中的那个纯正的词句。但是如果在某些事情上,我对你的解释感到怀疑,你必须原谅我。《圣经》是精深的,祈祷书是精深的,唔,你自己也是令人满意的,如果你肯把我们了不起的神学家写的那些久享盛誉的讲道文中的一部分读给我听的话,那是他们在精力旺盛时用心写成的。可是你必须原谅我,我那无能的年轻讲道人,如果我听了你那些不够完善的句子,一再重复的短语,虚假的怜悯,还有你的慢条斯理的讲话与抨击,你的嗯嗯呃呃,你的哼哼哈哈,再看到你的黑手套和白手绢,我竟然不住打呵欠的话。就我来说,这一切全无意义,时间太宝贵了,不应当这样浪费掉——但愿能避免这样,那多么好!
从事实际工作的教士时常会讲一番假话,说他们为需要宣讲的许许多多篇讲道文忙得疲惫不堪。这儿,我一定要对这种假话提出异议。我们都过分爱好自己的声音。一位传道师的虚荣心受到鼓动,要他凭听众非听不可的这一特权,使他自己的声音被人听到。他的讲道文是他生活中愉快的片断,是他自我振奋的得意时刻。“我这星期已经讲过九次道了。”前一天有位年轻的朋友对我这么说,他倦怠地举起一只手来揿着前额,真是一幅疲劳过度的殉道者的情景。“本星期九篇,上星期七篇,再上星期四篇。我这个月作了二十三篇讲道。这实在太受不了啦。”“真个的,真太受不了,”我打了一阵寒战说,“对随便哪个的精力来说,都太受不了啦。”“是呀,”他恭顺地回答,“真个的,是太受不了啦。我开始感到很吃力。”“我真希望,”我说,“你能够感到——我真希望可以使你感到。”但是他始终没有猜到,我心里为那些可怜的听众所感到的苦恼。
在我们提到的这一回,大伙儿听斯洛普先生讲道,至少并没有感到单调沉闷。他的题目对他的听众影响太大,不可能是乏味的。说实在的,斯洛普先生善于把字眼使用得很有力。在他的三十分钟滔滔不绝的讲道中,大伙儿全默不作声地洗耳恭听,不过眼睛里都闪射出愤怒的光芒,由一个激怒了的人传给了另一个,他们的鼻孔全大张着,愤慨的气息已经从里面喷射出来了。他们的两脚不住地移动,身子不安地摇晃,这表示他们思想紊乱,内心对全世界都感到激动不安。
在全体会众中,就数主教最为惊讶,他吓得头发几乎竖起来了。最后,他祝了福,祝福的方式压根儿赶不上他在自己书房里演习过那么久的那样,于是会众总算可以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