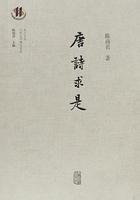
一
无论用古代的学术原则还是用现代的学术标准来衡量,康熙钦定的《全唐诗》都免不了因袭的干系——当代学者有机会见到胡震亨《唐音统签》全本和季振宜《唐诗》的三种不同的文本,经过认真的比读和分析,确信《全唐诗》只是将胡、季二书拼接合抄成一本书,从小传到校勘记作了粗糙的简化处理,就由十位在籍翰林在一年多时间内处理成现在见到的规模。《全唐诗》编纂期间所作唐诗增补,具有原创意义的其实只有从卷八八二到卷八八八的七卷补遗。但《全唐诗》毕竟是皇帝钦定的权威著作,成书三百多年来在唐诗研究和传播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影响至今不衰,且至今没有可以取代的著作。对此,真不知应该为前贤的成就感到骄傲,还是为当代学术感到遗憾。
《全唐诗》收诗缺漏,在其成书后不久,朱彝尊著《全唐诗未收书目》就有所指出,只是朱氏所举书目都据宋元书志,并非清代实存书目,即其所论没有任何的实际操作价值。其后二百多年,虽然名儒硕学层出不穷,但居然没有任何一位学者为《全唐诗》作具体的补遗工作。只有远在东瀛的学者市河世宁在编纂日本奈良、平安时期至镰仓以前汉诗为《日本诗纪》的同时,利用日本保存的典籍为《全唐诗》补遗,成《全唐诗逸》三卷,补录128人诗66首又279句。中国学者的唐诗辑佚工作,直到20世纪30年代,始有实际的展开。
从现有资料来看,最初从事唐诗补辑工作的是孙望先生。孙望(1912—1990),原名自强,字止畺,江苏常熟人。他在1932年进入金陵大学学习后,就从事唐诗辑佚工作,到1936年,成《全唐诗补逸初稿》七卷,得诗“二百七十有奇”。此稿当时曾有排印本刊布,在学术圈内形成一定影响,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称赞该书“于唐诗裨益匪浅,谨为学界庆贺”(据“百度百科”孙望条引录)。闻一多编《全唐诗汇补》《全唐诗续补》二书也曾据以编录唐人佚诗。此稿后经三十多年的增补,到1978年编成《全唐诗补逸》二十卷,共补诗830首又86句。其文献采据,以石刻文献、《永乐大典》和四部群书为大宗,较重要的收获有敦煌存一卷本王梵志诗,宋刊十卷本《张承吉文集》存张祜诗,清刊《麟角集》存王棨诗,清刊《丰溪存稿》存吕从庆诗,《永乐大典》存宋之问、王贞白佚诗等,以及《渤海国志长编》存中日交往诗。其中部分逸诗在1979年第1期《南京师范大学学报》刊发,笔者当时刚开始研究生学业,见到后深受启发,并就阅读中的疑问就教于孙先生,承他工楷详尽致覆,并在定稿中将拙见采入。前辈风范,令我至今感怀。
王重民(1903—1973),字有三,河北高阳人。他于1934年受北平图书馆派遣到英法作学术考察,又以互换馆员的身份到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次法藏敦煌遗书目录,有机会第一手完整接触这部分文献,1938年又赴英阅读伦敦博物院所藏敦煌卷子,先后历时五年,得以完成《补全唐诗》的初稿,复经王仲闻、俞平伯、刘盼遂等校阅,至1963年始刊布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在他身后整理遗稿时,又发现多种敦煌遗诗的抄校稿,并陆续予以发表。
闻一多的唐诗辑佚工作在他生前始终没有发表。直到199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十二卷本《闻一多全集》第七册收录徐少舟根据北京图书馆藏闻氏手稿整理的《全唐诗汇补》《全唐诗续补》二稿印出,其辑佚工作方为世人所知。两稿总约十五万字,均无序跋,仅《全唐诗汇补》卷首列有引用书目,凡二十八种。闻氏所谓汇考,是将《全唐诗》卷八八二至卷八八八补遗七卷也作辑佚看待,其体例显然是拟汇录自此以后各家的唐诗辑佚,因而将此七卷及《全唐诗逸》《全唐诗补逸》中诗尽量全部采入。他本人的新得佚诗数量不算太多,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已经将《翰林学士集》《会稽掇英总集》及敦煌遗书中诗有所采录。二稿显然为未完稿,若积以时日而能最终成编,必有可观。闻氏中年殉国,留下莫大的遗憾。
童养年(1909—2001),江苏睢宁人。原名童寿彭,字药山、药庵,号养年。1939年至1949年在原中央图书馆工作,1949年至1959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任编目组长,1959年至1988年在安徽大学图书馆工作,直到退休。他利用长期在图书馆工作的便利,日积月累,成《全唐诗续补遗》二十一卷。据作者前言所述,其书名为接续《全唐诗》原有补遗七卷而言,所得凡550家1 000多首,其采集文献范围极其广泛,尤以《古今图书集成》和地方文献为大宗,较重要的收获有《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存李郢自书诗卷存诗三十多首,《严陵集》存施肩吾、贯休等佚诗,《吴越钱氏传芳集》存吴越诸王诗集,《鉴诫录》存晚唐、前蜀大批佚诗等。
1982年,中华书局将王、孙、童三家辑佚稿四种结集为《全唐诗外编》出版,以王重民《补全唐诗》为第一编,以同人《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为第二编,以孙望《全唐诗补逸》为第三编,以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为第四编。各编有重复者,则以上述各编为次第,存前而删后;同一诗而出处不同者,则后见者存目。从全书来看,童辑删落较多。
《全唐诗外编》的出版,可以说是我国老一辈学者唐诗辑佚工作的结集,为学者提供了自《全唐诗》成书以后近二百八十年间中国学者辑录唐诗极其可观的收获,并在其后较长时间内,引起许多学者进一步考证唐诗和继续辑佚的兴趣。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该书发表的论文多达数十篇之多,足见其受关注的程度。当然,在肯定前辈辑佚成就的同时,也有必要看到各编都有一些重收误收的情况发生,其中童编问题尤多。
笔者1981年下半年在等待学位论文答辩期间,开始有关《全唐诗》的文献来源和文本订正的工作。由于知道已经有几位前辈完成了有关工作,最初并没有做唐诗辑佚的准备。直到1982年下半年见到新出版的《全唐诗外编》,欣羡前辈采辑丰备的同时,无意中发现在我曾阅读过的典籍中,似乎还有数量可观的唐诗未经采录,其中较大宗的即有《翰林学士集》存唐初佚诗48首(仅孙辑据《武林往哲遗书》录褚遂良3首),《会稽掇英总集》存唐人佚诗80多首。这些不过是我在读书中的无意发现,如果系统加以辑录,应该还会有可观的收获。此前研究生阶段曾从王运熙老师得悉目录书的体例和功用,又因读王梓坤院士在《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科学发现纵横谈》的论述,一方面根据《全唐诗》及《外编》确定前人编录唐诗之已用书目,根据唐宋书志了解唐人著述总目及在宋元明三代的流传存逸情况,再据《四库全书总目》和《中国丛书综录》确定唐宋典籍的存世总况;另一方面,则是模仿石油勘探,先取样确定资源之有无,再在面上铺开,以便作全面的采录。由于追求文献之全备、考订之深入、人事之推敲、真伪之鉴别诸方面都作了超过前人的努力,实际的收获远远超过最初的预想。1985年初完成《全唐诗续拾》初稿,得唐人逸诗2300多首,已经超过《全唐诗外编》的规模。1987年夏,中华书局编辑部在初审后,提出修改意见,并同时约请我修订《全唐诗外编》。这两方面工作历时一年,到1988年秋间交稿,1992年出版时统名为《全唐诗补编》,共三册,其中第一册为原《全唐诗外编》的修订本,孙、童两编都有较大幅度的删削,并在书末附修订说明逐一交代考订意见。后二册则为《全唐诗续拾》。全书收录唐五代佚诗大约6300首,而拙辑即达4600多首。能够有如此丰硕的所得,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在文献搜索范围和复核仔细方面,都较前人有所突破。其中如《文苑英华》《唐诗纪事》《万首唐人绝句》等基本唐诗典籍,在前人无数次工作以后再次利用现代索引手段加以检索,有新的发现。特别关注清中叶以后新见古籍的校核、近代以来新发现文物和典籍的追索,特别关注宋人得见而今已失传的唐代著作在宋元典籍中的遗存情况,特别关注长期被唐诗研究者忽略的一些似乎与唐诗文献没有直接关系的典籍中保存的唐诗文献。(二)重新界定诗文的界限,否定《全唐诗·凡例》认为佛道偈颂赞咒不是歌诗的偏见,将存世佛道二藏中的有关作品作了较彻底的清理。(三)利用了80年代中期一批学者唐诗辑佚的成果,其中尤以张步云、张靖龙、陶敏、汤华泉、邹志方、陈耀东、刘崇德、孔庆茂诸位采获较丰。我特别赞赏孙望先生在《全唐诗补逸》中对凡给自己工作以提示或启发的友人皆以说明的美德,在拙辑中坚持了这一体例。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限制,并没有能够充分利用当时已经发表的成绩。
拙辑《全唐诗补编》出版,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唐诗辑佚第二阶段成果的总汇。该书出版后,中外书评不少,基本给以积极评价,在此就不多说了。最近十年也陆续有些学者利用古籍检索手段予以纠订,这部分问题容到下节详谈。而本书最大的遗憾,是我的工作主要在上海进行,当时在敦煌文献方面仅能见到一部印得不太清晰的《敦煌宝藏》,因而于敦煌遗诗仅能据较清晰的写卷录一些相对有名作者的诗作,没有能力作完整的清理。
从1988年《全唐诗补编》定稿,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中国的学术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与唐诗辑佚工作关系密切的,一是敦煌文献文本的完整清晰影印和敦煌文献研究全面展开,二是域外文献和石刻文献大量发现、公布和研究,三是以《四库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和《中华再造善本》为代表的大量稀见公私典籍的印行。而最具有革命意义的则是古籍数码化完成古籍文本检索的普及化,使古籍辑佚检索更为便捷,鉴别重出互见更为准确,辨伪考订也可以更为精密科学。
最近二十年间在唐诗辑佚发掘方面最杰出的工作应该首推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首次完成了中、英、法、俄及散见敦煌遗诗的辑录,所录诗多达1 800多首,其中绝大多数为唐五代时期的作品,为《全唐诗》及《补编》未收之诗在千首以上。该书虽然没有采用以人存诗的编次方法,与《全唐诗》系列没有衔接关系,由于尽可能地依据原卷或较清晰的影印卷录文,各卷能注意保存原卷钞写时的面貌,于中外已有研究成果能较充分地吸收,在作品归属和作者考寻方面都尽了很大的努力,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平。如揭出李季兰上朱泚诗,补录《珠英集》中佚诗,根据文卷钞写起讫认定《补全唐诗》所收胡皓名下误收了另一佚名作者的几首诗,都是很重要的发现。稍感遗憾的是没有能够完成敦煌所存佛赞俗颂体诗歌的整理。稍后出版的张锡厚主编《全敦煌诗》(作家出版社,2006年),局部对徐书有所订补,总体则未有大的突破,且因不择手段地将本来一、二册书可以包含的内容,硬撑到二十册的规模,不仅影响该书的流布,而且也减损了其学术品位。
此外,最近二十年在唐诗文献方面较重要的发现有以下各项:(一)韩国所存旧本《夹注名贤十钞诗》收唐五代三十家七言律诗三百首,其中有百馀首佚诗,较重要的有皮日休、曹唐、李雄、韦蟾、吴仁璧等的作品。(二)俄藏敦煌遗书中蔡省风《瑶池新咏》残卷的发现,可以补录李季兰等女诗人的佚作,也让我们了解到这部唐代女诗人选本的大体面貌。(三)长沙窑瓷器题诗的更进一步发现。(四)日本古写本陆续有唐诗佚篇发现,尤以伏见宫存《杂钞》残卷存李端、崔曙、张谓、李颀等佚诗,后来曾编为《风藻饯言集》的圆珍送行诗卷,以及与鉴真东渡有关的几首佚诗,金泽文库藏香严智闲《香严颂》七十六首等,为较重要。(五)一些以往流通较少的古籍中,也有成批佚诗的发现,这里可以举到宋晏殊编《类要》残本、日本存宋刊《庐山记》足本、明刊《锦绣万花谷别集》等。(六)一些宋金元以及韩国人集句诗中保存的唐诗佚句,较零碎。